
图19-1 飞天 十六国 莫高窟第 272窟
飞天是佛教艺术中佛陀的八部侍从中之两部,即佛经中的乾闼婆与紧那罗。
乾闼婆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天歌神。由于他周身散发香气,又叫香音神。紧那罗也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天乐神。据唐《慧琳音义》,紧那罗“有微妙音响,能作歌舞”,与乾闼婆同在极乐国里弹琴歌唱,娱乐于佛。据说他们形影不离,融洽和谐,还是夫妻。我们通常所说的飞天,就是他们的合称,也就是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里所谓的“飞天伎乐”。总之,他们是佛国世界里具有特殊职能的“天人”①,而不是泛指六欲诸天和一切能飞的鬼神。
敦煌壁画和塑像中的飞天,与洞窟同时出现。从十六国开始,飞越了十几个朝代,历时近千年。直到元末,随着莫高窟的停建而消逝。在这十个朝代里,由于政权的更替,农业经济的发展,中西贸易的繁荣和文化交流频繁等历史情况的变化,飞天的形象、姿态,以及意境、情趣和形式风格,都在不断变化。千年间敦煌飞天形成了自己具有特色的演变发展的历史。
十六国时代飞天多出现在本生故事画主体人物的头上,虔诚地对舍身者的善行合掌敬礼(图19-1)。有的结队旋绕于窟顶藻井的四周,向着佛陀歌舞飞翔。有的好像镶嵌在平棋的岔角里,在适应固定的三角形壁面中取得形象的自由舒展。特别是佛陀背光中的飞天装饰带,两行小身飞天挥手起舞,互有呼应,在波状形的动律中袅袅上升,呈现出无声的节奏感。

图19-2 飞天 十六国 莫高窟第249窟
十六国的飞天,脸型椭圆,直鼻、大眼、大嘴、大耳,头束圆髻,或戴花蔓,或戴印度式三珠宝冠(图19-2)。她们身材粗短,上身半裸,腰裹长裙,肩披大巾,加上白鼻梁、白眼球,与西域石窟特别是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形象、姿态、色彩、线描和绘制过程均相似。敦煌飞天直接来自西域佛教石窟艺术,可称为西域式飞天。由于敦煌画家不熟悉新的佛教题材和外来的表现技法,运笔豪放而略粗犷,但却意外地带来了稚拙而朴质的美感。
北魏时代,飞天的活动领域扩大了。不仅在平棋的岔角里,主题性故事画和说法图的上方有飞天,在龛顶上还出现了飞天群,有奏乐者、有歌舞者。在中心柱四面龛上也出现了对称式的浮塑飞天行列,在平棋中心的莲池里,裸体天人在绿色的旋涡中游泳。
北魏飞天(图19-3、图19-4),虽然还保留着西域飞天的鲜明特点,但在具体的形象上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主要是受到敦煌地区根深叶茂的中原汉文化滋养,特别是魏晋十六国壁画造型的影响。飞天的脸型已由椭圆变为条长而丰满,眉平、眼秀、鼻丰、嘴小,五官匀称协调。身材比例逐渐修长,有的腿部相当于腰身的两倍。姿态亦多种多样,有的对面私语,有的横游太空,有的振臂腾飞,气度豪迈大方,势如翔云飞鹤。飞天起落处,朵朵香花满天飘扬,颇有“天花乱坠满虚空”②的诗意。

图19-3 飞天 北魏 莫高窟435窟

图19-4 飞天 北魏 莫高窟第248窟
北魏晚期到西魏,东阳王元荣从洛阳来敦煌出任瓜州刺史时期,改变了佛教艺术的流向,受到南朝神仙思想和艺术影响的中原佛教艺术开始向西传播。因而,敦煌壁画中出现了道教题材和佛教题材同在一窟的局面。既有佛教天人,也有道教神仙,其中有道教的羽人和飞仙,也有佛教的飞天。本来,飞天飞仙唐人多不分,但细察之仍有区别,飞仙出自道家,羽人即飞仙。在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羽人变为飞仙的过程,一方面羽人披上了飞天的大巾,另一方面是飞天抛弃了头后的圆光,这就出现了飞天的新形象:面貌清瘦,额广颐窄,脸上染两团赭红,鼻直眼秀,眉目疏朗,嘴角上翘,微含笑意。她们头束双髻,鬓发垂于胸前,肢体修长,手脚纤巧,着大袖长袍,或帔帛覆肩,长裙裹脚,在紫云浮空、天花旋转、“清虚明朗”的太空中翱翔。这就出现了从西域起飞、越过昆仑山、跨过大沙漠、冲过火焰山而进入玉门关的西域式飞天,与跨过长江黄河、翻过秦岭祁连、穿过河西走廊来到敦煌的南朝式的中原飞天,各以自己独特的风姿,同欢共乐在一个洞窟的艺术现象。自然,两者并存的不只是飞天,还包括其他题材壁画在内的两种不同意境和艺术风格的作品。
飞天和飞仙的区别是:飞天头后有圆光,无云彩,成群结队密集在一起,没有活动空间,空壁饰天花,境界是静的。飞仙头后无圆光(道教神仙一般无圆光),空间辽阔,境界开朗,云气漂流,天花旋转,境界是动的,两者意趣不同。然而,飞仙由飞天变化而来,飞仙是中国化的飞天,是佛道思想融合的反映。所以,不仅飞天进入坟墓,飞仙也闯进了石窟。
传自南朝的秀骨清像型飞天,实称飞仙,是从龙门石窟、邓县画像砖墓、麦积山石窟、天梯山石窟而来到莫高窟。本应称飞仙,隋唐以来飞天飞仙互用,从形象到境界都完全一致了。
北周仍然是一个短暂的鲜卑族政权,他们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又和西域通好。北周武帝娶突厥公主阿史那氏为皇后,发展中西贸易,促进了文化交流。因而,北周时代的飞天形象更加丰富多彩(图19-5至图19-9)。
旧的西域式飞天还盘旋在平棋的岔角里,新的西域式飞天又冲进了洞窟。或在说法图的上方,或挤进平棋岔角里,或凌空旋转莲花,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各司其职。新的西域式飞天脸圆、身短、体壮,头戴波斯式宝冠、身披大巾、着右袒僧祇支(衬衣),腰缠印度式大裙。最突出的是:面部和肉体的凹凸晕染,除了圆圜重叠晕染而外,还画白眉棱、白鼻梁、白眼眶、白牙齿、白下巴,有的在脸上、手臂、腹部高明处都画以白粉,不仅表现了圆滚滚的立体感,而且似乎闪闪发光。这种晕染法是龟兹壁画早期立体感表现手法,画史上称“天竺遗法”,北周时代几乎原样再次传入敦煌,成为新的西域式飞天的鲜明特征。
在许多北周洞窟里,中原式秀骨清像风格的飞天还没有退出洞窟,新的中原式飞天又已经崭露头角。在平棋的岔角里和藻井四周的飞天行列中,脸形方而丰满,即所谓“面短而艳”的形象出现了。她们两颊、额际、下巴均染以赭红,头束鬟,着汉式大袖长袍,展现出中原式飞天的新风貌。

图19-5 裸体飞天 北周 莫高窟第428窟

图19-6 飞天 北周 莫高窟第428窟

图19-7 飞天 北周 莫高窟第290窟

图19-8 飞天 北周 莫高窟第290窟

图19-9 飞天 北周 莫高窟第299窟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儒家、道家道德礼仪思想浸润、渗透的敦煌壁画中,第一次出现了裸体飞天。他们主要出现在平棋的岔角里,圆脸、直鼻、大耳,发呈波状,头顶鬟髻,下肢修长,男女生理性别分明。他们全身裸露,挥臂扭腰,脚尖指地,表现出激烈有力的舞姿。这与潇洒飘逸的西魏中原式飞天迥然异趣。
莫高窟艺术的早期,从十六国到北周的二百一十五年间,乾闼婆与紧那罗是同时出现的,但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和职能。乾闼婆比较自由,时而给佛陀张伞,时而为佛陀献花,时而栖身于花丛,时而翱翔于云霄。而紧那罗则不然,她们始终被禁闭在天宫楼阁里。天宫楼阁雕栏回曲,宫殿相连,其中有楼阁式的中国建筑,也有西方殿堂的圆拱门。盛装的紧那罗们,从宫门里露出半截身子,有的奏乐,有的跳舞,有的半开宫门,窥视人寰。她们衣冠形貌与乾闼婆相同,在绕窟一周的宫殿里,鼓乐竞奏,舞姿翩跹。到了北周,紧那罗冲破了天宫楼阁,腾空而起与乾闼婆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伎乐队伍。她们少则三五十身,有的吹笛,有的击鼓,有的弹筝,有的擘箜篌,有的 琵琶,有的托盘献花,有的挥臂跳跃,有的叉手扭腰,有的扬手散花,有的干脆盘倾鲜花,飞满天空。《法华经·譬喻品》里说:“诸天伎乐,百千万种于虚空中一时俱起,雨诸天花。”李白诗中也有所描写:“漫漫雨花落,嘈嘈天乐鸣。杏出霄汉外,仰攀日月行。”③这种舞乐相随、声色并举的场面,富有浓厚的诗意。还有龛楣中的伎乐,在莲花座上、忍冬丛中,拧腰甩胯、鼓掌踏足,表现出北方民族民间散乐(即歌舞百戏)的另一番情趣。
琵琶,有的托盘献花,有的挥臂跳跃,有的叉手扭腰,有的扬手散花,有的干脆盘倾鲜花,飞满天空。《法华经·譬喻品》里说:“诸天伎乐,百千万种于虚空中一时俱起,雨诸天花。”李白诗中也有所描写:“漫漫雨花落,嘈嘈天乐鸣。杏出霄汉外,仰攀日月行。”③这种舞乐相随、声色并举的场面,富有浓厚的诗意。还有龛楣中的伎乐,在莲花座上、忍冬丛中,拧腰甩胯、鼓掌踏足,表现出北方民族民间散乐(即歌舞百戏)的另一番情趣。
隋代是飞天最多、流行最广的时代,不仅寺院、石窟里画飞天,帝王宫廷里也雕刻飞天。隋炀帝在宫廷图书馆大门上挂有锦幔,为了卷起锦幔,在门上装置了两身木雕飞天,在门前地下巧设机关。炀帝行幸,宫人捧香炉前行,脚踩机关,则飞天自上降下,卷起锦幔徐徐上升。炀帝去后,飞天放下锦幔,恢复如故④。从这则记载可知,飞天不仅是供养佛陀的侍从,而且进入宫廷侍奉人间帝王。
由于上有好者,因而石窟里的飞天也越来越多了。人们一进洞窟,涌入眼里的,不仅是佛陀,更引人注目的是富有生命力的飞天(图19-10、图19-11)。

图19-10 飞天 隋 莫高窟第266窟

图19-11 弹箜篌 飞天 隋 莫高窟第276窟
隋代飞天,除了绕窟一周的宏伟行列外,又出现了龛顶自由活泼的飞天群。乾闼婆、紧那罗、羽人、乘龙持节仙人及雷神等,在同一天空各展风姿。在华盖式的藻井中心,过去是绿色宝池,现在是蔚蓝天空。有的在莲花中心画三只白兔,循环奔跑,互相追逐。莲花四周围绕一群飞天,其中有裸体童子,在彩云飘荡、天花旋转中起舞。正像敦煌变文中描写的:“化生童子见飞天,落花空中左右旋。”⑤这些画面表现了一个辽阔高朗的天空境界,也透露了净土思想的信息。
北齐黄门侍郎崔士顺所造佛堂的佛帐也有旋转飞天,记载中说:“帐上作飞仙右转,又刻紫云左转,往来交错终日不绝。”⑥这与隋唐飞天藻井创作意趣几乎相同。
隋代飞天脸型不一,有清秀型,也有条丰型。人体比例适度,腰肢柔软,绰约多姿。服饰也不一样,有上身半裸者,有着僧祇支者,有穿大袖长袍者。有不同的衣裙、冠饰和发髻,也有不同的表现方法,但就总体而言,正在探索中形成统一的时代风格。

图19-12 飞天 初唐 莫高窟第220窟
唐代的飞天进入一个新阶段(图19-12至图19-15)。龛顶和藻井四周仍然是飞天的活动领域,特别在龛顶,飞天自由地击鼓吹箫、轻歌曼舞。唐代变文给伎乐飞天配上了音调铿锵的赞美之辞:“无限乾闼婆,争捻乐器行。琵琶弦上急,羯鼓杖头忙。并吹箫兼笛,齐奏笙与簧。”⑦这些文字无疑增强了变文的欢乐气氛和艺术感染力。同时也说明了唐代飞天的乐舞结合的职能。

图19-13 飞天 初唐 莫高窟第321窟

图19-14 六臂飞天 盛唐 莫高窟第148窟

图19-15 飞天 盛唐 莫高窟第172窟
唐代飞天进入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净土变。表现“极乐世界”的净土变规模巨大,气势磅礴。往往在碧波荡漾的水国里,出现一片平台、曲栏和亭榭。上部碧空茫茫,下面烟波浩渺,远处水天相连,颇有海阔天空朗朗乾坤之感。飞天则活跃在蓝天之中: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如青蛙潜游水中;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双手抱头,从空中倒栽下来,势若流星;有的手托花盘,疾速地横跨长空。那在疾风中展卷的舞带,令人想起“排空驭气奔如电”的诗句。
盛唐时代的《极乐世界图》里,殿堂掩映,楼阁耸峙。飞天或挥舞长巾,曳带彩云,穿过重楼高阁,腾空而起。当她冲出楼阁已经升起,而长长的舞带和彩云还缭绕在穿过的楼阁中,蜿蜒起伏,势如游龙。飞天们奔腾自如,出没无常。特别是由角楼中冲出的飞天“霞帔曳彩虹”,凌空回首,很像唐代诗人韦渠牟《步虚词》中的仙女:“飘飘九霄外,下视望仙宫。”
唐代出现了双飞天:有的围绕宝盖,互相追赶,舞带彩云,漂流于空中,形成疾速旋转的圆圈;有的手挥莲蕾,并肩降落,袅袅的舞带在碧空中悠悠漫卷;有的一个在前面飞,一个在后面追,舞带彩云随风飘荡,前者回首呼应,扬手散花。当时大诗人李白咏仙女诗中有这样几句:“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这简直是唐代飞天的写照。可以认为:李白的诗是无形的画,敦煌飞天则是有形的诗。
唐代晚期的飞天,已由浓丽丰厚,逐渐转化为淡雅萧疏,极乐国里的飞天已经黯然失色。然而在悼念佛陀的悲剧场面——《涅槃图》里,他们从空而降,有的献上花环或璎珞,有的吹奏羌笛,有的献上一盘鲜花。在庄严静穆的表情中透露出沉郁悲哀的神情,体现了“天人共悲”的宗教境界。
唐代晚期的飞天,大半成群地集中在窟顶华盖四周。她们置身于翻滚的云彩中,有的卧乘彩云昂首飞驰,有的安坐在云堆里击鼓、吹箫,有的倒悬在云彩里挥手弹筝,有的舞蹈,有的散花,茫茫云海,五彩缤纷。正如敦煌变文中所描写的:“云中天乐吹杨柳,空里缤纷下落梅”⑧,又是一番境界。
五代宋初,曹氏画院的匠师们继承了唐代余绪,但在飞天的造型上,逐渐出现千篇一律的公式化倾向。只有露天的大型飞天,冲出了窄小的洞窟,活跃在悬崖峭壁间。远远望去,她们好像飞翔于林木葱茏的大自然里,似乎脱离佛国而进入了人寰。
西夏飞天,一部分沿袭宋式,一部分具有西夏独特风格。多脸形条长而颐尖,直鼻斜眼,头饰珠翠,世俗性较浓。但舞带短而身量沉重,飘浮飞动感不强。其中童子飞天则裸体而丰肥,着抹肚、穿红皮靴,别具风格(图19-16)。
元代流行密教,藏密无飞天,唐密飞天亦极少。有一类飞天,作女童形象,头饰二童髻,帔巾长裙,衬托着一片黄云,手持长茎莲花,眼视前方,情态含蓄(图19-17)。虽然缺少轻盈缥缈的动的韵律,却具有另一种意趣,即元人诗中所谓的“神仙可有情缘在,手掉芙蓉欲赠谁”⑨的意味。
敦煌飞天,经历了千年岁月,展示了不同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许多优美的形象、欢乐的境界、永恒的艺术生命力至今仍然吸引着人们,给人以审美享受。

图19-16 飞天 西夏 莫高窟第97窟

图19-17 飞天 元 莫高窟第3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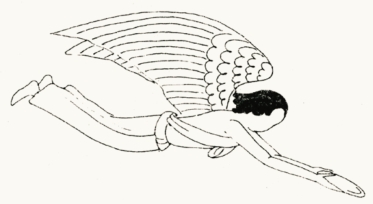
图19-18 天使 前5世纪希腊银币
 (https://www.xing528.com)
(https://www.xing528.com)
图19-19 希腊后期天使 (相当秦汉时)

图19-20 罗马天使 前2世纪 受胎神告

图19-21 希腊后期天使 (相当秦汉时)
飞天是一种具有特殊职能的飞神,这样的神东方西方都有。西方为天使。公元前四、五世纪,希腊银币上即有臂上长着翅膀的上身半裸的童子(图19-18)。希腊高脚铜镜上也有展开双翼、凌空飞翔的裸体儿童(图19-19)。在基督教壁画中,天使的形象,有天真活泼的裸体儿童,长着等身翅膀,成群结队地飞翔在空中或嬉戏于圣母的身边(图19-20、图19-21)。而多数则是妙龄少女,披长发或戴金冠,着锦衣,束裙或着小腿裤,肩上搭长巾,臂生双翼,头后有圆光。这种西方艺术家创造的天使形象也传到东方,传到中国,而且进入了佛教寺院和石窟。斯坦因在新疆磨朗佛教寺院遗址中发现二、三世纪的壁画中有长双翼的半身西方天使。麦积山景明三年的壁画中有臂生双翼的俗装仙人。新疆发现的7世纪的舍利盒上,有着更多的双翼裸体童子天使。直到元代,扬州保存的罗马拉丁文碑上还刻着中国少女式的天使,仍然长着两只翅膀。但西方的天使并未在中国繁衍,也没有在佛教艺术中落户,只不过偶尔露面而已。
天使,是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里传达天帝意旨的特殊使者。天使的形象是西方艺术家发挥高度想象力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他们把不能飞的人和善飞的鸟结合在一起,使机灵而不能飞翔的人具有鸟的飞翔本领。但是,在固定羽翼的控制下,追求真实感和人情味的西方天使,往往缺少轻盈、灵活而优美的舞姿和遨游太空的精神境界。这种艺术想象与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不尽相同。
中国原本有一种具有特定职能的飞神,叫羽人(图19-22至图19-25)。按照宋人洪兴祖的解释,“羽人即飞仙”,即“上升九霄,飞行上清”⑩的天仙。这种羽人是导引人羽化升天、长生不死的神。这类艺术形象,汉晋墓室壁画中可以看到:画瘦骨嶙峋老人,衣裙、袖口装饰着羽毛,飘飘凌空。汉代画像石中也有“耳出于顶”臂生双翼的仙人,而下身往往化为云龙,浮游太空。对中国式的羽人的审美观并不是没有变化的,东汉王充对此已有新的看法,他说:“飞者皆有翼,物无翼而飞,谓之仙人。”11《神仙传》中也说:“仙人者,或束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浮游青云。”12可见早在汉代,对遍身长绿毛或臂生羽翼的飞仙,认为不算真正有本领的神仙,也不认为美,因而在墓室壁画中已有所改变。到西晋时代,神仙家葛洪讲得更明确:“仙童仙女来侍,飞行轻举,不用羽翼。”并且认为“古之得仙者,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本,更受异形”13。“失人之本”即降低了人为万物之灵的本质。因此,西方生双翼的天使,我国遍体长绿毛的神仙,在中国都没有发展起来。而出现的新形象是:男则多为高冠大袍,女则鬟髻彩裙,不生毛,不长羽翼,不腾云彩,仅在衣服的领袖裙边作毛羽之饰,浮游于星辰云气之中。南北朝时期,在佛教思想与神仙思想互相融合的过程中,飞天和羽人的形象同时出现在南朝的墓室和敦煌石窟的壁画中(图19-26至图19-29)。佛教飞天和道家的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仙融合为一,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飞天,那就是不长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主要凭借一条长长的舞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

图19-22 羽人 汉 武班祠画像

图19-23 羽人 汉 武班祠画像

图19-24 石棺羽人 北魏 河南洛阳出土

图19-25 羽人 北魏 麦积山第115窟

图19-26 羽人 西魏 莫高窟第249窟

图19-27 羽人化飞天 西魏 莫高窟第285窟

图19-28 羽人 丹阳 南朝大墓砖刻壁画

图19-29 天人 丹阳 南朝大墓砖刻壁画

图19-30 哈迈石刻飞天 印度 公元前2世纪晚期

图19-31 石刻说法图上飞天 印度 3世纪
敦煌飞天,是印度飞天中国化的产物,但印度飞天有多种形式,有头戴宝冠臂生双翼的早期飞天,有头束大髻上身半裸斜披络巾,依托云彩的女性飞天,有头戴金冠,裸体、腰悬遮羞布,肩披长巾,不乘云彩的石刻飞天,在壁画集中的阿旃陀石窟中,飞天都不披长巾(图19-30至图19-34)。

图19-32 飞天 印度阿旃陀第2窟

图19-33 飞天 印度阿旃陀第2窟

图19-34 说法相上飞天 犍陀罗雕刻
敦煌飞天不是直接来自印度而是经过阿富汗和新疆龟兹石窟辗转传入敦煌的(图19-35至图19-39)。因此,敦煌飞天是多种艺术因素的合成形象,然而她们却显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一方面决定于内在思想上的佛与仙的融合,一方面是形式美创造上的独特成就。这主要体现在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等方面。

图19-35 飞天 阿富汗 3世纪

图19-36 飞天 阿富汗巴米扬

图19-37 飞天 新疆若羌磨朗遗址

图19-38 飞天 新疆克孜尔石窟

图19-39 飞天 新疆克孜尔石窟
敦煌飞天的创作方法,与敦煌壁画总的创作方法一样。它经历了形象思维一系列的历程:现实、想象、意象、艺术形象。现实——歌舞伎、百戏;想象——无翼而飞。这就体现了中国绘画美学思想中的“寓形寄意”“立象以尽意”,甚至“得意忘象”等等重意象、重意境的特色。因而敦煌飞天是古代画师根据现实生活形象,加上主观想象——联想、迁想和幻想并倾注思想感情,熔铸而成的意象的显现。它具有中国人的风貌和神采,不长翅膀、不生羽毛,却无男女生理特征。尽管乾闼婆与紧那罗是夫妻,也都化成非男非女的无性仙人。去掉佛教天人头上的灵光圈,使有限的艺术形象,从本身的微妙变化以及其遨游驰骋的辽阔空间,给人以新的“无限之意”的美感。这就是作为中国飞天的代表——唐代飞天的艺术成就。
艺术意象必须有以相适应的表现方法和技巧,才能使它表现为客观的艺术形象。对敦煌壁画来说,中国民族民间绘画突出的特色之一——线描造型,在飞天的创造中得到充分体现。
当然,以线造型不只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埃及壁画以粗壮而一致的土红线描绘花鸟人物,两千多年前的希腊瓶画用挺劲的黑线塑造简略的人物形象。印度绘画也以线描勾描轮廓,但浓重的色彩使线的造型功能没有充分显示出来,波斯细密画线描有严密的组合,但那是受到中国画影响的新成果。所有这些绘画的线描,都与中国画线描的功能和形态意趣不同。敦煌壁画的线描,始终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艺术语言。中国特殊的富有弹性的毛笔,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在描线时,运笔、运力、运情三者融为一体。描线时在抑扬顿挫、轻重徐疾的变化中产生的笔情墨趣,形成一种复杂的互相交织的节奏感和韵律感。飞天的飞动感,一方面为形象本身的动势所决定,同时潇洒飘逸的线描,也有助于形象的运动感。特别是舞带上最后描上去的白线,大大加强了舞带在空中展卷翻飞的意趣。而飞天长长的舞带和云彩,造成了线描技术上的高难度。敦煌壁画线描上的艺术成就,突出地体现在飞天上。飞天的艺术生命力,决定于最后的定形线。由于敦煌画家具有深厚的线描功力,线描的艺术成就充分体现在飞天上。飞天的民族风格主要特点之一,又体现在线描上。
唐代飞天,是极乐世界里最活跃的神灵形象。这首先取决于意象、意境的孕育和设计,除线描之外,关键在于形、线、色三者的结合和协调。飞天形象塑造的第一步,是摆好位置落墨起稿。早期起稿是用土红线粗略地画出姿态动作的主体轮廓。唐代用淡墨起稿,比较准确细致,基本上画成一幅白描,然后敷彩。敷彩时浇色饱满,涂色自由,渲染叠晕,浑若天成。起稿线往往被色彩掩盖,定形线不拘成墨,往往与起稿线不相符合。这说明画师们在壁画制作过程中不断修改、不断完善,致使色下线、色上线或隐或显、互相交错,形成一个形色线浑然一体的复合形象。这不仅不影响飞天形象的准确性和神情风采的表现,而且更显得工致而不死板,放逸而不粗糙,有灵活而含蓄的意趣。这正是敦煌壁画风格上的特点,也是敦煌飞天富有艺术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敦煌飞天,不是印度飞天的翻版,也不是中国羽人的完全继承。以歌舞伎为蓝本,大胆吸收外来艺术营养,促进传统艺术的变革,创造出表达中国思想意识、风土人情和审美思想的中国飞天,充分展现了新的民族风格。
注释:
1 天人:佛教泛指一切能飞的神灵。飞天能飞,但有特殊职能,可以称为天人,但天人不一定是飞天。
2 《心地观经》第一。
3 李白:《登瓦官阁》。
4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十年至十一年。
5 北图殷字62号《阿弥陀经讲经文》。
6 (元)《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中。
7 《敦煌变文集》卷下《维摩诘经讲经文》。
8 《敦煌变文集》卷下《目连救母变文》。
9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神仙部》,(元)《李伯时射姑仙像卷》。
10 《淮南子》引《仙经》。
11 《论衡·道虚篇》。
12 《神仙传·彭祖传》。
13 《抱朴子》内篇卷四。
(原载《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