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体制内纪录片的发展历程
独立纪录片的概念与意涵本身代表了一种相对性,在对它进行理论阐释的同时,将其置于其相对概念——体制内纪录片的参照框架之下对于阐释体系的客观性与完整性至关重要。这两个方面的对比,将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中国独立纪录片与中国体制内纪录片各个发展阶段在整个发展的历程中处于怎样的坐标系,两者发生互动的阶段以及独立纪录片之“独立”对于体制内制作的纪录片来说究竟如何体现。因此,在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进行梳理之前,本小节尝试对“独立”的相对所指——中国体制内纪录片的发展历程进行必要的交代。
一、体制内纪录片的历史梳理
1.从“宣教”到“纪实”——纪实主义美学兴起
1958年10月1日,第一部电视纪录片诞生,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周年》。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纪录片创作必须要反映热情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生活,发挥社会主义事业这一“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语)的作用。电视纪录片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模式,包括鲜明的先行主题、说教式的长篇解说、各行其是的声画关系等。这一时期,从以“报道”方式纪录重大事件的《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到歌颂生产战线英雄的《金溪女将》,到改革开放后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再到《雕塑家刘焕章》,是一个逐步摆脱主题化的纪录模式的过程。
1990年代上半期被称作电视纪录片的“纪实期”,新现实主义兴起,伴随而来的是对中国纪录片有着深远影响的巴赞的“纪实美学”理论。该理论强调电影的独特魅力在于完整地再现和未加修饰的现实。克拉考尔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了电影的纪录本性,规定电影的本性是“物质现实的复原”。新电影纪实理论的不断被介绍与引入,唤醒了国人对纪录片本体意识的觉悟。1991年《望长城》的出现,作为个体的人在影像中出现了,这部纪录片被称作开创了中国“纪实主义”纪录片的先河。紧随其后,《沙与海》、《藏北人家》、《家在向海》、《最后的山神》等纪录片精品的出现,使纪实主义的创作观念在很大的范围内深入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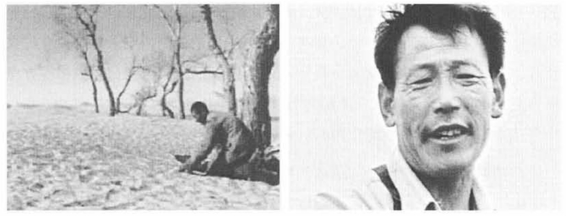
图2-1 《沙与海》

图2-2 《藏北人家》

图2-3 《最后的山神》
这一时期,纪实主义标举的人文关怀精神,使创作者们开始将镜头对准平民大众,对准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这里,中央电视台14993年《生活空间》的开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生活空间》采用现场跟踪的方式纪录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小人物的日常经验折射出时代的变化,这一点填补了中国纪录片的一个历史盲点。同时,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以及北京电视台《纪录》等纪录片类栏目也相继出现。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的体制内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有过一段短暂而珍贵的交叉与融合。两者不仅在题材选择、创作风格等方面极为类似,同时纪录片人也在体制内与体制外自由地穿插,在这种积极地互动中将“纪实主义”美学深植于中国的纪录片创作中。
2.遭遇困境——栏目化问题与“体制”之困
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电视纪录片创作开始走入低谷,纪录片创作陷入了困顿。这种困顿是几个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第一,市场化、商业化的冲击。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各个行业都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激荡。在整个媒体世界被市场化后,纪录片也不可避免地被推向了市场。栖身于媒体的纪录片能够找到的最有效对策就是纪录片栏目化。这一对策所形成的创作环境与1990年代前期形成了鲜明对比。之前的纪录片创作是在一种近乎理想与完美的环境下进行创作的。纪录片作为当时衡量电视台品位水准高低的重要参数,受到各个电视台的自上而下的重视:划拨高额经费、抽调精兵强将、自由地使用设备和安排时间、无须担忧创收问题。创作者得以全神贯注于纪录片的艺术探索与创新。而栏目化之后,这种宽松自由的创作模式不复存在。密集的播出周期,轮轴转的快速生产,与纪录片相对较长的制作周期形成尖锐的矛盾,而且栏目对节目时长的统一规划,限制了创作者的艺术思维。随着这种模式的深化,势必形成纪录片选材、结构、剪辑上的机械复制,类如工业化批量生产流程造成了纪录片的千人一面。同时,纪实主义美学的过分强调带来对于“纪实”手法的生硬搬用以及跟风效仿,使电视纪录片开始走入了模式化的死胡同。北京电视台《纪录》栏目制片人陈大立在谈及当时的纪录片时说:“那个时候一想起纪录片,大家想到的就是对一个人的跟踪,镜头摇晃,节奏缓慢,大段的长镜头,大段不紧不慢的访谈或对话,解说词声调不高,冷静而有距离感……打开很多电视台的纪录片类栏目,都是如此,似乎纪录片只有这一种拍法。”[2]另外,商业大潮的来袭,对于纪录片这一耗时耗财又鲜有回报的片种来说冲击是最大的。在收视效益的追赶下,纪录片的创作不得不常常在创作时间与费用上处处精打细算,这种束缚与纪录片的自由创作形成了根本性的矛盾,结果必然损伤纪录片的真实性与艺术性,降低纪录片的品质。
第二,体制的约束。在中国,电视台作为党和政府重要的舆论喉舌,决定了作为编导的个人活动空间是有严格的规定与约束的,这种模式长此以往有可能磨损创作者的主动性,形成职业化的惰性。纪录片能否顺利播出关乎对编导成绩的肯定,也关系着实际的物质利益。规范的约束使编导在创作中不容易放开手脚,为避免涉及一些尖锐问题,而失却了对事件及生活表象下真实的探讨。同时,电视台的纪录片创作者与社会、民众的距离在加大。随着媒体事业的不断发达,媒体工作人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为优越的阶层,自身的生存状态与他们的拍摄对象——大众之间的距离在渐渐增大。而如果不能使自己真正深入到民众之中,就很有可能导致作品停留于事件或人物的表面与平面,而流于对现实生活的浮光掠影式的采集。这一阶段的作品与其称作“纪录片”,不如说更像“纪实”类节目。在此期间,栏目化的电视纪录片的收视率急剧下滑。典型的实例比如当年曾创下36%的收视率、比电视剧更火爆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如今收视率已暴跌至7%—8%;北京电视台《纪录》栏目的收视率也仅有4%—5%;云南电视台《云南纪事》栏目的收视率平均值仅在2.5%左右[3]。
3.创作的转向——机构化系列纪录片
由于怀斯曼的“直接电影”观念与小川绅介纪录精神的引入,中国的一些纪录片人不再满足于栏目化纪录片这种名为纪录片实则是“纪实节目”的制作,一部分人开始考虑进行体制外的纪录片创作。事实上,电视纪录片的创作群体由此向着三个方向分化:一部分人脱离电视台而成为真正的独立制作人;一小部分人仍旧留在电视台,但从纪录片栏目中调出,专门负责为电视台制作获奖的纪录片,这是一个中国独有的创作状况,并且往往是电视纪录片中精品的主要来源;第三部分的制作人则继续在电视台进行栏目化纪录片或者称为纪实节目的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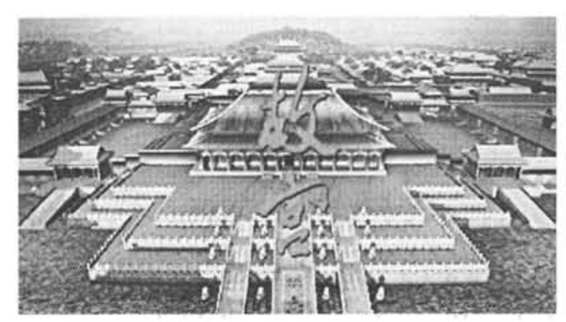
图2-4 《故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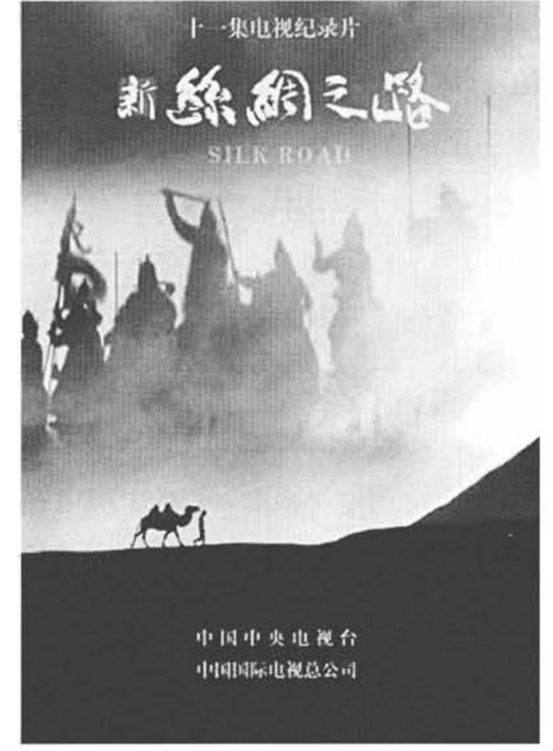
图2-5 《新丝绸之路》
随着各种电视纪实栏目的收视率急遽下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栏目化的运作模式对纪录片创作的限制。电视媒体适时地开始调整纪录片的创作布局,不再将拍摄与播放栏目化纪录片作为重要日程,而在维持着这些纪实性栏目的同时,开始利用国家媒体的巨大资源与权威优势,选取一些重大社会或历史题材,进行系列的大型纪录片的创作,由此诞生了如《故宫》、《郑和下西洋》、《新丝绸之路》、《大国崛起》等优秀纪录片作品。这些纪录片创作,与国际接轨,并且站在了国际纪录片制作的前沿。目前国际纪录片创作普遍地分为两类:机构化的系列纪录片和个人化纪录片。当前国内电视台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制作与国际上机构化的系列纪录片极为相似,而个人化纪录片的创作阵营,就中国的当下情况而言,个别地存在于电视媒体中一些为获奖纪录片专设的部门,大多已不再存在于体制之内,而转移到体制之外的独立制作的阵营之中。(https://www.xing528.com)
二、体制内外的交融与区隔
虽然体制外与体制内本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但在中国,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它们的关系非但不可能绝对对立起来,还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裂的联系。无论从早期创作者当时的身份归属,还是后来与体制内的多次合作,再到体制内外纪录片创作趋向的融合,独立纪录片与体制内纪录片始终存在着各种关联,在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中,体制内与体制外在各自的发展中又有着多种形式的交叉。
1.体制内外的合作
体制外的创作者在纪录片的创作中呈现着对体制内“反叛”的同时,又主动或被动地与体制内发生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与互动。一方面,体制外从体制内获得各种重要支持;另一方面,体制内也从体制外获得了积极的推动力。
(1)体制外创作寻求或接受体制内的支持
与西方的纪录片创作环境不同,在中国没有公共基金或是文化基金给纪录片以赞助,在这样的境况下,艰难生存于体制之外的独立纪录片创作者常常主动或被动地借用体制内的资源完成自己的创作。尤其是早期的创作者们一直以来与体制内保持着合作关系。从早年的独立纪录创作的作品比例上看,很大一部分作品都与体制内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比如,《流浪北京》[4]、《天边》、《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八廓南街16号》、《天安门》[5]等。
隶属于或曾隶属于电视台的创作者康健宁、段锦川,在中央台做片子的吴文光都曾“蹭”电视台的机器拍自己的作品,有时也利用体制内的优势和便利拍摄一些特殊的场景以供自己的独立创作所用。另外,他们有时接受电视台的资金拍一些要求上相对宽松的作品。1990年代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部在完成国家有重大活动的时候拍摄专题片等主要任务之外,申报项目资金时会安排另一组人员拍摄内容上要求比较宽松的纪录片。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本属于为宣传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这一重大活动的政府计划,申报的同时让段锦川“套拍”其他几个片子,对他以什么形式拍不干预,于是段锦川在一年的时间里接连拍了《天边》、《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八廓南街16号》三部纪录片作品[6]。其中《八廓南街16号》1997年完成后一直没有得到播映,直到2001年才在央视一套的栏目中播出,却以从100分钟被裁减为30分钟长度作为代价。
另一次与体制合作的有益尝试是在1997年。当时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纪录片部出资300余万元[7]筹拍《时代写真》系列纪录片,当时确定的十位导演中有电视台的,也有少数独立纪录制作人。这套片子允许有较长的制作期,有比较高的预算,由参加拍摄的人自己报选题,通过就可以拍,没有给出具体的限制。这些纪录片是:段锦川的《沉船》,内容关于1997年有人旨在用于爱国主义教育,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打捞甲午战争时期被日军击沉的邓世昌所乘之舰“志远号”;蒋樾的《三峡的故事》,内容为三峡拆迁在即,分别住在河对岸的一对年轻夫妇的故事;云南电视台卢望平的《党支部》,关注一个云南信教地区,当地党支部和基督教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宁夏电视台康健宁的《公安分局》,关注一个公安分局的日常生活;四川经济台梁碧波的《三节草》,关注一个四川姑娘嫁到彝族地区,当了土司夫人的风风雨雨历程;中央电视台陈晓卿的《大哥大桑塔纳破小褂》,关注致富人群的生活;云南电视台郝跃骏《最后的马帮》,关注了云南省最后一支国营马帮。[8]这是体制内与体制外一次重要的互动,不仅使体制外的独立制片人得到一个难得的创作机会,同时更是让体制内的创作者们获得一次绝佳地展露个人才华的机会。这些创作者们除了段锦川与蒋樾是独立纪录片人之外,其他都是各个电视台的编导。这些电视台的编导虽然身份归属体制内,同时倚靠电视台的资金支持,但这次电视台对创作没有提出具体限制的绝佳机会,也让体制内的优秀纪录片人得以言由心生,以自由的意志在纪录创作中过了一把瘾。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体制内与体制外创作者一同创作的集合,并且形成了在水平上相当整齐的一批纪录片。
(2)体制内借重体制外的“灵感”与推动
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刚开播的时候,制片人卢望平(曾担任《流浪北京》的摄像)曾安排将蒋樾拍摄的《东方三峡》、《上班》、《票友》等短纪录片在其板块《生活空间》中播出,使《生活空间》逐渐摆脱了开播初期“生活服务类”节目的定位。这次被认为是独立纪录片与所谓的体制之间“最成功的一次互动”[9],间接地催生了中国纪录片纪实主义美学的高潮。因为在此之后,接任的制片人陈虻将《生活空间》正式定位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创作了一批关注普通人生活、尊重个体生命的优秀纪录片,引起观众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巨大成功。体制内由此开始确立了“民众”纪录片的地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纪实主义纪录片的创作潮流。时间说:“要不是蒋樾,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他不是这样的讲法。不是他纪录片的语言,就不会在《东方时空》的每个栏目里渗透,不是他我们纪录片的语言不会这么迅速地规模宏大地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10]

图2-6 《生活空间》
事实上,这种在体制内与体制外自由转换的角色在早期的创作者身上比较普遍。不过从整个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来看,这只是一个阶段的局部现象,随着电视台纪录片普遍的栏目化,留给体制外纪录片作品的空间越来越小。
2.体制内外创作趋向的融合与分化
在体制内的电视纪录片与体制外的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中,除各自发展之外,也有过创作观念、纪录风格的交融的时期。
1990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和消费社会来临的新形势下,以理性思辨的精英文化为主导的高雅文化丧失了主流地位。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型,社会群体意识日益隐退,个体意识不断觉醒。在文化界,新现实主义在中国兴起,与之相伴的巴赞的纪实主义美学在中国的纪录片创作中刮起了狂飙。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之下,一批回归纪实主义本性的纪录片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在体制内与体制外迅速生长起来。在这一时期,体制内外的纪录片不约而同地确立了同一个“反叛”对象:1990年代之前电视纪录片的宏大叙事和“政论”模式,创作呈现了空前一致的纪录话语。将镜头对准民众,对准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关注弱势群体,体现普遍的人文关怀,注重纪录生活的原生态等等,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创作几乎共同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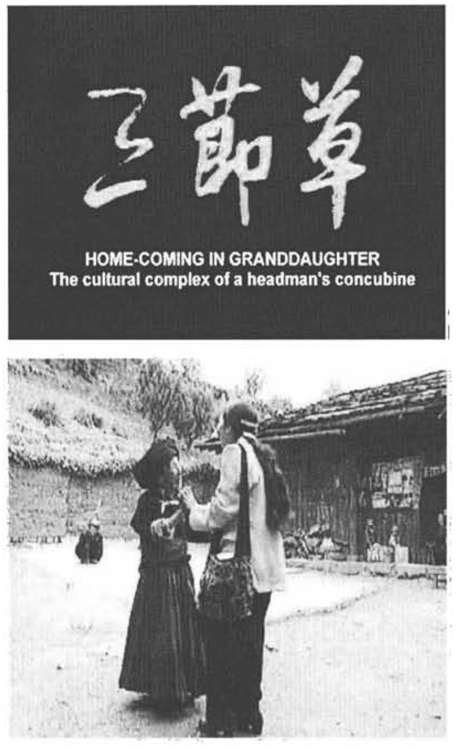
图2-7 《三节草》
陈虻谈当年《生活空间》开播时说:“我给《生活空间》定下的创作宗旨就是:表达的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在此基础上去实现一种‘人文教化’,或者说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引导人们去进行思考,从而建立起一种更加合理的人际关系。”这一时期涌现的独立纪录片《阴阳》、《彼岸》、《回到凤凰桥》等,与同一时期的体制内纪录片《藏北人家》、《舟舟的世界》、《龙脊》、《三节草》等,从题材选择到纪录风格都体现着相当的一致性。从《阴阳》里的徐文章、《彼岸》里的临时话剧演员、《回到凤凰桥》里的小保姆,再到《藏北人家》里的藏北牧民、《舟舟的世界》里的弱智儿童舟舟、《龙脊》里的农村小学生潘纪恩和潘能高、《三节草》里的摩梭族妇女,他们无不是处于社会底层甚至边缘的人群。而且对于这些对象的生存际遇都进行了客观原生态的关注,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深入的批判与反思。
随着中国电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商业大潮的侵袭,“经营”意识迫使体制内的栏目不得不考虑节目所能创造的商业价值,体制内原本精英立场的精品创作在商业化的运作下逐渐萎缩。随着央视栏目《生活空间》的更名[11],电视纪录片的定位开始趋向趣味性与故事性,加之独立制作人与体制之间的越来越艰难的磨合,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这次空前的交叉合流,在昙花一现后也终于宣告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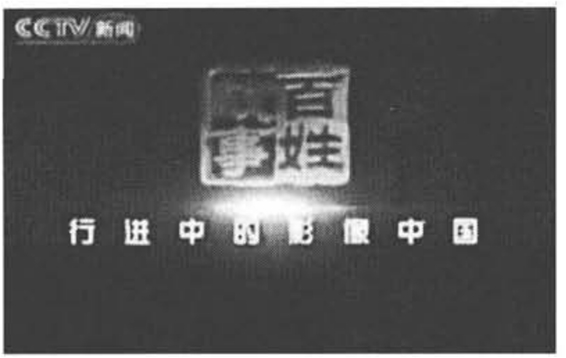
图2-8 《百姓故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