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风格(仪式)化与写实(自然)化 |
按照肯·丹西格尔的说法,“对于观众来说,最明显的风格特征来自于构成性元素:机位、运动、人或物的前后景并置、光线照明、声音,当然还有剪辑”。这代表了对于电影导演艺术风格的狭义化理解。其实,从更加广泛也更加全面的角度来看,电影导演艺术风格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题材和故事的选择;(2)主题的偏好与开掘;(3)银幕场面调度(视觉总和及其含义);(4)演员的选择与表演风格;(5)音响;(6)剪辑节奏,等等。正是这些元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电影导演艺术千差万别的风格,而在千差万别的风格当中,风格(仪式)化与写实(自然)化是两种主要的风格倾向,两者之间的对立与互动高度体现了辩证法逻辑的精妙。
应该说,风格化意味着极端化,将任何一种风格特质推向极致都会形成风格化,即使是将写实、自然和非风格化的倾向推向极致,也会形成风格。在风格化(仪式化、程式化、符号化或形式感)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丹麦电影大师卡尔·德莱叶。按照美国著名影评家宝琳·凯尔的说法,“卡尔·德莱叶的艺术开始绽放之处,恰恰是绝大多数导演最终放弃的地点”。德莱叶在《圣女贞德》中对形式化的坚持和极致表达,最精确地印证了凯尔的这一论断。《圣女贞德》全片运用特写,对此,观众先感到语境的缺失,然后是对特写的强烈关注。德国电影大师茂瑙和“纪录电影之父”弗拉哈迪联合拍摄的《禁忌》(Tabu,1931),以仪式化的形式展示了南太平洋海岛上充满图腾与禁忌的纯朴生活。这一风格后来在苏联导演卡拉托佐夫的黑白片《我是古巴》(I Am Cuba,1964)中,演变成对于加勒比海拉丁风情的形式化赞美。

图5-3 《禁忌》画面
苏联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的《祖先的影子》(Shadows of Forgotten Ancestors,1964)和《石榴的颜色》(The Color of Pomegranates,1968)等影片所体现的浓烈的民族风格(传说故事、仪式性静态画面和装饰性色彩构图),使之成为世界影坛上无法被专制意识形态摧毁的一朵奇葩。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绍拉在《卡门》(1983)、《弗拉门戈》(Flamenco,1995)和《探戈》(Tango,1998)等影片中,借用典型的西班牙音乐和舞蹈形式,程式化、符号化地体现了热情奔放的拉丁文化。画家出身的英国导演彼得·格林纳威则在《画师的合同》(The Draughtsman’s Contract,1982)、《枕边禁书》(The Pillow Book,1996)和《情欲色香味》中将电影影像的绘画风格发挥到极致。塔尔科夫斯基的《安德烈·鲁勃廖夫》(Andrei Rublev,1966)开场的“铸钟”段落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和象征意味,被张艺谋所借鉴,在《红高粱》中演化为颇具中国特色的“祭酒”(仪式)段落。日本导演大岛渚的《仪式》(The Ceremony,1971)和韩国导演李在容的《丑闻》(Scandal,2003),执著于各自民族性的视听形式与叙事内涵的探索,造就了各自鲜明的风格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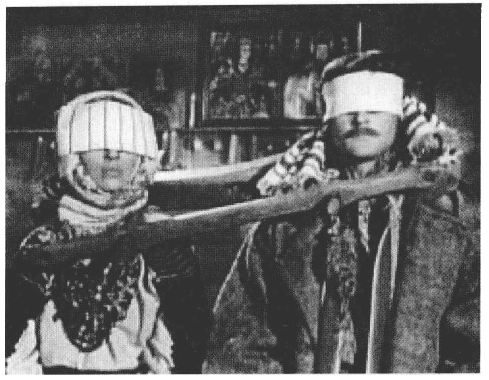
图5-4 《祖先的影子》画面
就极端风格化的表达方式而言,后现代电影可以看做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不管是在题材和思想内涵,还是叙事、时空、声画、剪辑和节奏等方面,其混乱、杂糅、暴虐和激情都体现出后现代文化消解与重构的典型风格。奥利弗·斯通的《天生杀人狂》中极端暴力的仪式化作秀,巴兹·鲁尔曼的《罗密欧与茱丽叶》中古典爱情的后现代演绎,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的《罪恶之城》(Sin City,2004)中的黑白影像、仪式化动作和节奏,以及塔伦提诺的《杀死比尔》对于暴力和复仇的仪式化崇拜与迷恋,都可以算作是电影艺术风格化的最新成果。
与风格(仪式)化相对立的写实(自然)化倾向从电影诞生起就一直存在,并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实践中和安德烈·巴赞的倡导下成为一种主要的电影美学传统:摈弃人为化风格,还现实以本来面目,强调冷静客观的写实手法。罗西里尼(《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和《游击队》)、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和《擦鞋童》)和维斯康蒂(《大地在波动》和《罗科和他的兄弟》)在战后意大利的废墟上开创了写实风格的先河,而布列松(《乡村牧师日记》)、安东尼奥尼(《奇遇》)、特吕弗(《四百下》)、新藤兼人(《裸岛》)、奥米(《木屐树》)、侯孝贤(《风柜来的人》)、贾木什(《天堂陌影》)、阿巴斯(《樱桃的滋味》)和贾樟柯(《小武》)等人则秉承了这一写实(自然)化倾向。
如果说以上两类导演终其一生坚持自己在电影风格上的选择的话,另有一些导演则为自己不同的电影选择了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风格。早期的德国表现主义大师弗朗兹·朗格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1927年的《大都会》以典型的表现主义仪式化风格表现了工业社会人类的异化,而1931年的《被诅咒的人》却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写实风格。比利·怀尔德曾盛赞朗格的这部影片:“《被诅咒的人》具有电影应有的视觉外观,看似是新闻片。你绝不会意识到它是搬演的,就像新闻片一样,你指望抓住瞬间的真谛并加以开发利用。”[5]1]怀尔德还坦承自己的成名作《双重赔偿》受到了《被诅咒的人》的深刻影响。(https://www.xing528.com)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身上。冯·提尔是“九五教义派”的灵魂人物,主张极端的写实和自然手法(实景拍摄、DV手提摄影、同期声和无剧本的现场发挥等),其作品《白痴》(The Idiots,1998)完全实践了“九五教义派”的美学主张,逼真地纪录了一群青年精英对于“正常”社会的反叛,与《家庭聚会》、《敏郎悲歌》和《国王不死》并称“九五教义派”创世作品的“四大金刚”。不过,冯·提尔在2000年拍摄的《黑暗中的舞者》(Dancer in the Dark),却在写实题材中加入了风格化的歌舞与抒情表达,而接下来的《狗镇》(Dogville,2003)则完全走向了“九五教义派”的反面:极端的舞台化、写意化、简约化和抽象化,将影片推向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表演形式,其目的是让观众忽视电影的外在形式,聚精会神地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内涵的表达上。将风格化推向极致,恰恰可以消解风格,这与将非风格化(无风格)推向极致而成为风格,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再次彰显出辩证逻辑的惊人魅力。
风格(仪式)化与写实(自然)化的对立统一既可以表现在不同的导演身上,也可以表现在同一个导演的不同影片上,还可以表现在特定导演的同一部作品当中。库布里克是一位能够将仪式化与写实化两种对立的风格熔于一炉的导演大师,《光荣之路》用逼真的纪实手法再现了法军对蚁山的自杀性攻击,战争的残酷和恐怖令人触目惊心;而处决士兵的过程,则采用了完全仪式化的表现手法,传达出死亡带来的痛苦的高贵感和残忍的荒诞感,并强化了权力的腐化与生命的虚妄。30年后,库布里克又在反映越战的《全金属外壳》中重新将风格化的镜头语言与写实化的表演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影片开场海军陆战队教官对新兵长达六分钟的几近虐待、强暴式的训斥段落就是如此。
在当今世界主流影坛,将纪录电影叙事化和戏剧化成为一种电影创作浪潮(所谓的Docudrama就是典型代表),但英国BBC电视制片人出身、极具创新意识的导演彼得·沃特金斯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叙事电影纪录化,在《战争游戏》(The War Game,1965)和《惩罚公园》(Punishment Park,1971)中创造出逼真和震撼的艺术效果。沃特金斯在1999年拍摄的影片《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1871)将叙事电影的纪实性元素推向极致,同时也融入了写意和表现性的风格元素(类似于拉斯·冯·提尔的《狗镇》),使该片成为逼真性纪实与表现性写意的一种奇妙的悖论式融合体(辩证性的对立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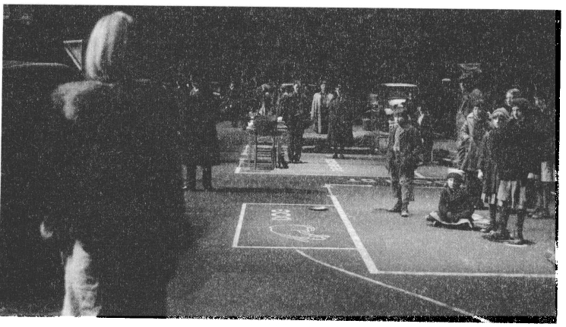
图5-5 《狗镇》画面
纵观电影历史,这种纪实与反纪实、仪式与反仪式、风格与反风格的悖论式融合体在特定的情况下,往往会产生极为惊人的艺术效果。兰妮·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1934)用高度纪实化的电影语言展示了仪式化的纳粹党代会,将现实中的希特勒、国社党和第三帝国军队塑造成德国的神灵与救世主,成为此后意识形态宣传和宏大叙事模式的典范。而小津安二郎则在《东京物语》这样的小品式电影中,将日本文化中的泛仪式化行为(尊卑长幼和言谈举止)与自然流畅、宁静淡泊的视听语言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东方电影的一代宗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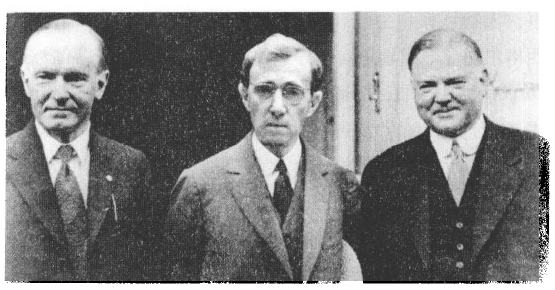
图5-6 《变色龙》画面
此外,长期被低估的伍迪·艾伦的影片《变色龙》(Zelig,1983)也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经典例子。影片讲述了一个奇人雷纳德·泽利格(伍迪·艾伦饰)的故事,他的神奇之处在于可以随时随地地将自己的外形容貌和言谈举止变得跟周围人一样,跟希特勒在一起就可以变成纳粹党徒,跟中国人在一起就可以变成龙的传人。伍迪·艾伦极为巧妙地采用了纪实(仿纪实或伪纪实)手法,将实拍的画面与历史名人的新闻片画面以假乱真地剪接在一起。这样一来,《变色龙》就在风格化与纪实性方面呈现为一个有机而自在的整体,关于风格与非风格的论题似乎也在此失去了现实的依托和假设的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