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文字学者在讲汉字构造的时候,一般都遵循六书的说法,把汉字分成象形、指事等六类。
“六书”一语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地官·保氏》列举了周代用来教育贵族子弟的“六艺”的项目,其中有“六书”:
……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但是《周礼》并末具体说明六书的内容。
汉代学者把六书解释为关于汉字构造的六种基本原则。《汉书·艺文志》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郑众注《周礼·地官·保氏》说:
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许慎《说文·叙》还给六书分别下了定义,并举了例字: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今本作“察而可见”,《段注》据《汉书·艺文志》颜注改),“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诎”通“屈”。“诘诎”的意思就是曲折),“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一般认为前一句指形旁而言,后一句指声旁而言),“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谊”通“义”),以见指 (“
(“ ”通“麾”。“指麾”在这里当“意之所指”讲),“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说文》以“老”为会意字,训为“考”。“考”字在“老”部,“从老省,丂声”,训为“老”)。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通“麾”。“指麾”在这里当“意之所指”讲),“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说文》以“老”为会意字,训为“考”。“考”字在“老”部,“从老省,丂声”,训为“老”)。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汉代的经学家分古文和今文两派(参看〔四(三)〕)。《周礼》是古文学派的经典。上引《汉书·艺文志》是根据西汉末年古文学派大师刘歆的《七略》编成的。郑众和许慎也都属于古文学派。郑众是郑兴的儿子,郑兴是刘歆的学生。许慎是贾逵的学生,贾逵的父親贾徽也是刘歆的学生。所以上引这三家的六书说应该是同出一源的。不过在六书的名称和次序上,他们之间却有一些差别,情况如下表:
后人多数袭用许慎的六书名称。
《周礼》把六书跟九数并提,二者都是儿童学习的科目。九数就是九九表,六书的内容也应该很浅显,恐怕只是一些常用的文字(参看张政烺《六书古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刋》第十本)。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经学派的“托古改制”。
六书说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汉代学者创立六书说,对文字学的发展是有巨大功绩的。作为六书名称的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等术语,直到今天大家都仍然在使用。但是汉代在文字学发展史上毕竟属于早期阶段,汉代学者对汉字构造的研究不可能十全十美。而且为了要凑“六”这个数,他们在给汉字的构造分类的时候,显然很难完全从实际出发。因此六书说的问题也是相当多的。下面把几个主要问题简单介绍一下。先讲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的问题,再讲转注的问题,最后讲假借的问题。
按照六书说,用意符造成的字,即我们所说的表意字,分成象形、指事、会意三类,但是这三类之间的界线实际上并不明确。
《说文·叙》说“日、“月”是象形字,“上”、“下”是指事字。“日”、“月”本作 “上”、“下”本作
“上”、“下”本作 、
、 。前者所用的字符象实物之形,所代表的词就是所象之物的名称。后者用的是抽象的形符,所代表的词不是“物”的名称,而是“事”的名称。这两类字的区别似乎很明确。但是,实际上却有不少字是很难确定它们究竟应该归入哪一类的。例如
。前者所用的字符象实物之形,所代表的词就是所象之物的名称。后者用的是抽象的形符,所代表的词不是“物”的名称,而是“事”的名称。这两类字的区别似乎很明确。但是,实际上却有不少字是很难确定它们究竟应该归入哪一类的。例如 (大)这类字,它们所用的字符跟“日”、“月”一样也是象实物之形的,可是所代表的词并不是所象之物的名称,而是跟所象之物有关的“事”的名称,这一点却跟“上”、“下”相近。因此讲六书的人有的把这类字归入指事,有的把这类字归入象形。《说文》说:“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似乎许慎自己是把“大”看作象形字的。许慎还把某些用抽象的形符构成的字也看作象形字。例如《说文》对
(大)这类字,它们所用的字符跟“日”、“月”一样也是象实物之形的,可是所代表的词并不是所象之物的名称,而是跟所象之物有关的“事”的名称,这一点却跟“上”、“下”相近。因此讲六书的人有的把这类字归入指事,有的把这类字归入象形。《说文》说:“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似乎许慎自己是把“大”看作象形字的。许慎还把某些用抽象的形符构成的字也看作象形字。例如《说文》对 (叕)字的解释就是“缀联也,象形”(秦简“叕”字作
(叕)字的解释就是“缀联也,象形”(秦简“叕”字作 写法跟《说文》有别,许慎对“叕”字字形的解释不一定正确,但是这一点在这里无关紧要)。《说文》里的“叕”字以六条曲线相缀联示意,这跟“上”、“下”以短线跟长线的位置关系示意,有多大区别呢?“叕”可以算象形字,“上、“下”为什么就不能算象形字呢?郑樵在《通志·六书略》里就把“上”、“下”归入象形中的“象位”类,这样做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这样一来,象形、指事的界线实际上就荡然无存了。
写法跟《说文》有别,许慎对“叕”字字形的解释不一定正确,但是这一点在这里无关紧要)。《说文》里的“叕”字以六条曲线相缀联示意,这跟“上”、“下”以短线跟长线的位置关系示意,有多大区别呢?“叕”可以算象形字,“上、“下”为什么就不能算象形字呢?郑樵在《通志·六书略》里就把“上”、“下”归入象形中的“象位”类,这样做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这样一来,象形、指事的界线实际上就荡然无存了。
《说文·叙》给会意举的例子是“武”、“信”。“武”本是从“止”从“戈”的字。“止戈”为“武”,是说能使战争停止才是真正的“武”。“人言”为“信”,是说人讲的话应该有信用。但是在上古文字里,这种跟后来的“歪”一类字相似的、完全依靠会合偏旁字义来表意的字,是非常少见的。《说文·叙》举出的这两个字都有问题。现代学者大多数认为“信”本是从“言”“人”声的形声字(唐兰先生认为从“人”“言”声)。“武”字见于甲骨文,是出现得很早的一个字。“止戈为武”的说法出自《左传》(见宣公十二年),历史相当古,但是这种思想显然不是当初造“武”字的人所能够具有的。在上古文字里,用两个以上意符构成的表意字,多数是使用形符的,字形往往有图画意味,如我们在〔三(二)〕里举过的“立”、“步”等字。讲六书的人多数把这种字看作会意字,但是它们的性质跟“歪”一类会意字显然是有区别的。郑樵在《六书略》里把“立”和“步”列入象形字。他说“立”字“象人立地上”,“步”字“象二趾相前后”,解释字形比《说文》高明。近人林义光在《文源》里更明确主张,只有像“止戈为武”、“人言为信”那样“取其词义连属”的字,才可以算会意字,像 (射)、
(射)、 (涉)、
(涉)、 (舂,象两手举杵舂臼中物)、
(舂,象两手举杵舂臼中物)、 (争,象两手争一物)等字那样,“随体画物,其会合也不以意而以形”的字,都应该算象形字。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其会合也以形”的字,在会合两个以上意符来表示一个新的意义(即跟所使用的各个意符本身所表示的意义不相同的一个意义)这一点上,却跟“日”、“月”一类象形字不同,而跟“其会合也以意”的会意字一致。所以把它们算作会意字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汉字已经变得完全不象形之后,人们有时还在用“其会合也以形”的办法造合体表意字,也就是说把义符硬当作形符用。例如以“人”在“水”上表示漂浮之意的“氽”字,就是很晚才造出来的。这种字应该看作象形字呢,还是应该看作会意字呢?总之,会意跟象形的界线也是不明确的。
(争,象两手争一物)等字那样,“随体画物,其会合也不以意而以形”的字,都应该算象形字。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其会合也以形”的字,在会合两个以上意符来表示一个新的意义(即跟所使用的各个意符本身所表示的意义不相同的一个意义)这一点上,却跟“日”、“月”一类象形字不同,而跟“其会合也以意”的会意字一致。所以把它们算作会意字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汉字已经变得完全不象形之后,人们有时还在用“其会合也以形”的办法造合体表意字,也就是说把义符硬当作形符用。例如以“人”在“水”上表示漂浮之意的“氽”字,就是很晚才造出来的。这种字应该看作象形字呢,还是应该看作会意字呢?总之,会意跟象形的界线也是不明确的。
还有些表意字的性质,跟《说文·叙》为象形、指事、会意所举的例字都显然不同,例如某些所谓变体字,即“叵”一类的字(“叵”的意思是不可,字形就是反写的“可”)。很多人把这种字归入定义比较模糊的指事类,这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还有一些人把这种字归入会意类,这就跟《说文》给会意所下的定义显然矛盾了。
有些用六书说分析表意字结构的人,还想出了什么“象形兼指事”、“会意兼指事”等名目,适足以说明六书说划分表意字类别的不合理。(https://www.xing528.com)
六书中的转注,问题更大。“转注”这个名称的字面意义,在六书中最为模糊。《说文·叙》对转注的解释也不够清楚。因此后人对转注的异说最多。下面举少数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简单介绍一下。
1,以转变字形方向的造字方法为转注 宋元间的戴侗(《六书故》)、元代的周伯琦(《六书正讹》)等主张此说,认为“反正( )为乏(
)为乏( )”等转变字形方向的造字方法就是转注(唐代裴务齐《切韵序》说“考字左回,老字右转”,以“考”、“老”二字最下部一笔走向的不同来解释这两个字的“转注”关系。一般把裴氏看作以字形转向为转注的说法的创始者。但是他对“考”、“老”二字的解释过于荒谬,所以后人极少袭用)。
)”等转变字形方向的造字方法就是转注(唐代裴务齐《切韵序》说“考字左回,老字右转”,以“考”、“老”二字最下部一笔走向的不同来解释这两个字的“转注”关系。一般把裴氏看作以字形转向为转注的说法的创始者。但是他对“考”、“老”二字的解释过于荒谬,所以后人极少袭用)。
2,以与形旁可以互训的形声字为转注字 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繫传通释》)等主张此说,认为转注字“类于形声”,但一般形声字不能与形旁互训,如“‘江’、‘河’可以同谓之‘水’,‘水’不可同谓之‘江’、‘河’”,而转注字则可以与形旁互训,如“‘寿’、‘耋’、‘耄’、‘耆’可同谓之‘老’,‘老’亦可同谓之‘耆’,往来皆通”(见徐、书卷一“上”字注。徐氏的转注说比较复杂,这里只取主要的意思)。
3,以部首与部中之字的关系为转注 清代江声(《六书说》)等主张此说。江氏说:“《说文解字》一书凡五百四十部,其分部即‘建类’也,其始‘一’终‘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即所谓‘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属皆从某’,即‘同意相受’也。”
4,以在多义字上加注意符滋生出形声结构的分化字为转注 清代郑珍、郑知同父子等主张此说。郑知同《六书浅说》谓“转注以声旁为主,一字分用,但各以形旁注之。转注与形声相反而实相成”,如“齊”(齐)字滋生出“齋”(斋)、“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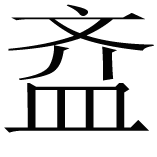 )、“劑”(剂)等字,就是转注({斋}、{
)、“劑”(剂)等字,就是转注({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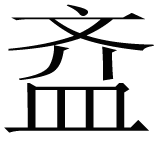 }、{剂}等词本来都用“齐”字表示)。
}、{剂}等词本来都用“齐”字表示)。
5,以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意符或音符造成繁体或分化字为转注 清代饶炯(《文字存真》)等主张此说。饶氏说:“转注本用字后之造字。一因篆体形晦,义不甚显,而从本篆加形加声以明之(引者按:如〔三(二)〕中举过的“ ”加“水”而为“淵”之类)。是即王氏《释例》(指王筠《说文释例》)之所谓累增字也。一因义有推广,文无分辨,而从本篆加形加声以别之(引者按:如上条所举“齐”加形旁而为“斋”、“齍”、“剂”之类)。一因方言转变,音无由判,而从本篆加声以别之。是即王氏《释例》之所谓分别文也。”他认为“考”字就是由于“方言有变‘老’声而呼‘丂’者”,因而在“老”字上“加‘丂’以别之”而造成的。
”加“水”而为“淵”之类)。是即王氏《释例》(指王筠《说文释例》)之所谓累增字也。一因义有推广,文无分辨,而从本篆加形加声以别之(引者按:如上条所举“齐”加形旁而为“斋”、“齍”、“剂”之类)。一因方言转变,音无由判,而从本篆加声以别之。是即王氏《释例》之所谓分别文也。”他认为“考”字就是由于“方言有变‘老’声而呼‘丂’者”,因而在“老”字上“加‘丂’以别之”而造成的。
6,以文字转音表示他义为转注 宋代张有(《复古编》)、明代杨慎(《转注古音略》)等主张此说,认为文字转读他音以表示另一意义就是转注。例如:“其”本“箕”字初文,转音而用为虚词“其”。“少”本读上声,转读去声而用为少年之“少”。
7,以词义引申为转注 清代江永(《与戴震书》)、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主张此说,认为文字的本义展转引申为他义就是转注。例如:命令之“令”转为官名之“令”。长短之“长”转为少长之“长”,又转为官名之“长”。
8,以训诂为转注 清代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主张此说,认为文字展转相互训释,或数字同训为一义(如《尔雅·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就是转注。
9,以反映语言孳乳的造字为转注 章炳麟(《转注假借说》)等主张此说。章氏说:“盖字者孳乳而寖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 ,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他认为如“屏”和“藩”,“亡”和“无”等等,彼此音相转而义相通,虽然字形没有联系,同样可以看作转注的例子。
,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他认为如“屏”和“藩”,“亡”和“无”等等,彼此音相转而义相通,虽然字形没有联系,同样可以看作转注的例子。
以上诸说,大都显然跟汉代学者的原意不合。第一、六、七、八、九诸说所说的转注,跟《说文》所说的转注毫无共同之处。其中,第七、八、九诸说其实是在讲语言学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值得研究的,但是放到作为“造字之本”的六书的范围里来,却只能引起混乱。第三说几乎把所有的字都纳入转注的范围。这种说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毫无意义的。第二说也许比较符合《说文》的原意。但是按照这种说法,转注字只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形声字,似乎没有独立为一书的必要。而且严格说起来,“老”字跟“考”、“寿”、“耋”、“耄”、“耆”等字也并不是完全同义的。提出第四、五两说的人,大概认为一般的形声字是直接用意符和音符构成的,所以把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偏旁而成的形声字另称为转注字。其实形声字大部分是通过加注偏旁而形成的,把这种形声字跟一般的形声字分开来,是不合理的。如果只把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音符而成的形声字称为转注字,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意符而成的形声字则仍称为形声字,那倒还能使形声跟转注的区分显得合理一些。不过这跟《说文》的原意大概也是不符合的。
我们认为,在今天研究汉字,根本不用去管转注这个术语。不讲转注,完全能够把汉字的构造讲清楚。至于旧有的转注说中有阶值的内容,有的可以放在文字学里适当的部分去讲,有的可以放到语言学里去讲。总之,我们究全没有必要卷入到无休无止的关于转注定义的争论中去。
《说文·叙》给假借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似乎跟我们所说的假借(借用某个字来表示跟这个字同音或音近的词)完全相合。其实并不然。因为《说文·叙》所举的假借例字是“令”、“长”,它们只能用来说明词义引申的现象,而不能用来说明借字表音的现象。主张转注就是引申的清代学者,就把“令”、“长”移作了转注的例字。
大概汉代学者心目中的假借,就是用某个字来表示它的本义(造字时准备让它表示的意义)之外的某种意义。至于这种现象究竟是由词义引申引起的,还是由借字表音引起的,他们并不想去分辨。也有可能他们根本不承认在“本无其字”的假借里,有跟词义引申无关的借字表音现象。从《说文》喜欢把借字表音现象硬说成词义引申现象的情况来看(参看〔九(五)1A〕),后一种推测大概是正确的。但是,跟词义引申无关的“本无其字”的借字表音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从普通文字学的角度,还是从汉字的事实来看,都必须承认这一点(参看第一章)。词义引申是一种语言现象,借字表音则是用文字记录语言的一种方法,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就具体的例子来看,由词义引申引起的和由借字表音引起的一字多用现象,有时的确很难分辨。但是从原则上说,却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所以,否认借字表音现象的存在是错误的;把由词义引申引起的和由借字表者引起的一字多用现象混为一谈,都称为假借,也是不妥当的。
在古代的文字学者中,已经有人指出了把词义引申跟借字表音混同起来的不妥当。例如戴侗在《六书故》里就明确提出了假借不应该包括引申的主张。他解释假借说:“所谓假借者,义无所因,特借其声,然后谓之假借。”因此他认为“令”、“长”不能用作假借的例字,像“豆”字本来当一种盛食器皿讲(俎豆之“豆”),又借为豆麦之“豆”,这才是真正的假借。把转注解释为引申的文字学者,大体上也把引申跟假借区分了开来。
但是清代以前的文字学者绝大多数是把引申包括在假借里的。即使是已经比较明确地认识到词义引申和借字表音这两种现象的不同性质的人,多数也还是这样做。例如:戴震认为“一字具数用”有“依于义以引申”和“依于声而旁寄”两种情况。旁寄应该就是指借字表音而言的。但是他仍然主张把引申和旁寄都称为假借,反对把引申从假借里分出来(《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见《戴东原集》)。
现在,有不少人仍然把引申跟假借混为一谈,有的人并明确主张在本无其字的假借里不存在跟词义引申无关的借字表音现象。可见汉代学者的假借说直到今天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前面说过,汉代学者提出六书说是有功劳的。但是六书说在建立起权威之后,就逐渐变成束缚文字学发展的桎梏了。在崇经媚古的封建时代里,研究文字学的人都把六书奉为不可违离的指针。尽管他们对象形、指事等六书的理解往往各不相同,却没有一个人敢跳出六书的圈子去进行研究。好像汉字天生注定非分成象形、指事等六类不可。大家写了很多书和文章,争论究竟应该怎样给转注下定义究竟应该把哪些字归入象形,哪些字归入指事,哪些字归入会意等等。而这些问题实际上却大都是争论不出什么有意义的结果来的。可以说,很多精力是白白浪费了。另一方面,文字学上很多应该研究的问题,却往往没有人去研究。直到今天,这种研究风气对我们仍然还有影响。这是值得警惕的。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说:“……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第一、它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各人可有各人的说法。其次,每个文字如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那一类。单从这两点说,我们就不能只信仰六书而不去找别的解释了。”这段话也许说得有点过头,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