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类社会的良心”——独立纪录精神
“剧情片营造着五光十色的‘白日梦’,纪录片却能担当人类社会的‘良心’。”[33]纪录精神是“对人的真诚平等的尊重和倾听,是对生活真相的敏锐、勇敢的探索和质疑。”[34]
贾樟柯在其文章《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再次到来》中对于独立电影与独立电影人的理解同样可以用在独立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人身上:
总是在电影处于困难之时,总是在电影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总是在文化信心不足的时刻,独立电影以其批判与自省的独立精神、不拘一格的创新力量从事着文化的建设。
这是一群真正的热爱者,有着不可抑制的电影欲望。他们因放眼更深远的电影形态而自然地超越行业已有的评价方式。他们的电影方式总是出入意料,但情感投注又总能落到实处。他们不理会所谓专业方式,因而获得更多创新的可能。他们拒绝遵循固有的行业标准,因而获得多元的观念和价值。他们因身处陈规陋习之外而海阔天空,他们也因坚守知识分子的良心操守而踏实稳重。[35]
独立纪录片人身为有着深切的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本着人文主义的立场对“人本”的充分尊重下,往往采取了对现实生活长期关注的方式,发掘着纪录片的真实,坚持着这个超越了功利的“寂寞”事业。
一、对“人本”的尊重
从“人文主义”的传统来看,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有三点:第一,人文主义聚焦在人的身上,一切从人的经验开始。第二,每个人自身都是有价值的,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第三,人文主义始终对思想十分重视,首先,思想不能孤立于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来形成和加以理解;其次,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替个人经济利益、阶级利益或者性的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本能冲动作辩解。[36]
人文主义的核心在于对人的尊重。这种尊重最根本的要落实于“平等”二字,而“平等”对于纪录影像而言,意味着无论对象属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无论他的职业、性别、种族、年龄、肤色及信仰,都应当有权利得到影像的“观照”,同时应当被平等地对待,也正是这种精神使纪录片获得了尊严。正如中国首届独立影像展的主题词——“从最低的地方开始拍摄”所说,独立纪录片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的选材对象涵盖了许多在以往的影像中不曾出现的人物和事件,他们的对象可以是工人、农民、农民工,也可以是乞丐、盲流甚至是三陪小姐、同性恋。在创作者看来,他们与自己是完全平等的鲜活的生命,与自己一样有着理想与情感,应该得到平等地对待与观照。不管是缘于对主流影像视角与题材的突破与反叛,还是出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或者是出于“社会良心”,独立纪录片人总是将占社会最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作为自己纪录的对象。这点在90年代后期的非职业创作群体中有着集中的体现,如杜海滨的《高楼下面》中的农民工,杨荔娜的《老头》中的城市中的老年人,《远山》、《八矿》中的矿工等。这一阶段,“关注底层”以及“人文关怀”成为观者尤其是研究者们给予独立纪录片的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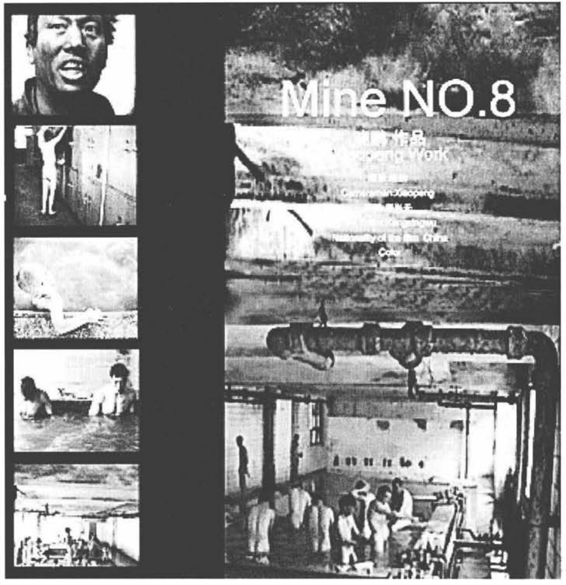
图3-6 《八矿》
事实上,将纪录片的视线投向这些所谓底层的人群、普通的百姓,并不必然意味着纪录片就已体现了对被拍摄对象的人本尊重。一些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尽管将普通百姓纳入被拍摄对象的行列,却常常因“塑造”人物的定式,将人物原本的生命轨迹描述为创作者思维定式中的或是符合宣教需要的一幅图景在近几年的话语氛围中,这种所谓“关怀”“关注底层、边缘”的论调越来越受到人们尤其是创作者们的质疑。这些语词在很多人看来代表了一种俯视的视角从高处落到低处的“关注”与“关怀”。很多独立纪录片所普遍呈现出来的并不仅仅是对底层、边缘人群的一种关注,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完全平等的交往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同时,对于这些处于艰难生活境地的非主流人群的纪录,创作者并非着力呈现他们的苦难,而是立体地勾画了他们有悲亦有喜的生活画卷,探讨与追寻了人类共同的人生命题。
实际上,在独立纪录片的创作中很多人的出发点,在于自己拍自己。他们大多把这些拍摄者看作与自己同样的人,同样普通的生命,甚至很多创作者认为自己是与被拍摄者处于同一生存状态之中的人,他们与这些纪录对象的关系是一种自然的亲近,同一境况中的惺惺相惜。朱传明曾自述:“有人问我是如何同一个弹棉花的人交上了朋友。其实同他一样,我也来自民间,来自底层,是一种民间的情感与力量使我们血脉相通,是一种民间的血缘使我们无所不谈”[37]。黄文海认为自己跟所拍的纪录片中的人物状态是一样的:“你跟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一样的,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社会压力和存在于你身上的是一样的。我离开中央电视台后,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同样会感觉到:如果我没有办暂住证的话,我一样也会害怕警察的。再就像《梦游》里的那些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多多少少都在我的身上也发生过,我和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一样的。”[38]也正是出于中国独立纪录片人不约而同地对“人本”的尊重,使他们大多采取了“直接电影”的客观纪录方式,以使纪录片中的人物得到直接电影大师阿尔伯特·梅索斯[39]所说的“体面和尊敬的对待”[40]。
与独立纪录片不同,虽然自“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栏目为开端,电视媒体的纪录片较之以往在很大程度上贴近了被摄对象,尤其是普通百姓。但是身为电视媒体记者的纪录片创作者与被摄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因经济、权力的掌握的不对等而产生的距离,他们对普通百姓的接近,很容易停留在较为浅表的层次,同时由于后来纪录片栏目化之后运作时间的限制也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创作者进入现实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以主流媒体为背景的纪录片往往容易在面对“模范”的仰视和面对“平民”的俯视间难以平衡。
二、“时间”——沉淀的生命与现实
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认为“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信条。这个“时间”就是拍摄人在现场实际工作的时间单元,它决定了所纪录的内容和含金量[41]。他创作纪录片的过程以“尽可能呆在现场”最为著名,很多影片的拍摄时间至少三到五年之久。小川的纪录片《三里冢之夏》、《三里冢:第二道防线的人们》、《牧野村千年物语》,无一例外地坚持了“时间”的信条。而1975年,小川绅介移居山形县上山市牧野村,既耕田又拍摄农民生活,竟然在那里生活了15年。对真相的探索依赖于“在场”的纪录之眼,完整呈现出创作者所目击到的真实现场,这种现场是不可复制和还原的。

图3-7 《三里冢之夏》
“要是你觉得你的纪录片做得不够好,肯定是你贴得还不够近。”这是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名言,而“贴近”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纪录片人冯艳被小川绅介十几年拍摄《三里冢》的经历所打动。她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小川绅介关于纪录片的书籍所涉及的内容主要不是如何去拍摄和剪辑,而更多的是如何深入生活,深入民众。这个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博士将小川绅介的《收割电影:小川绅介的世界》一书翻译成中文后,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独立纪录片的创作中。在她拍摄纪录片《长江之梦》期间,她对小川绅介关于纪录片创作的“时间”的概念有了自己的实践和体会:“一个一个村子找,拍工地,没完没了地拍那些人的怨言,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拍的东西根本不一样。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它必须有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看一些成熟的导演拍的大片,不是很舒服,因为他们已经把人定性了,然后找适合他的观念的人物,用他们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是反过来的。”“这次是第一部,接下来还有第二部、第三部,一直跟踪这些人,通过这些人可以看到中国的现实:永远的开发和人的关系。”[42]她的后面一部纪录片《秉爱》更是让时间的力量在纪录片中得以充分的展现。《秉爱》的拍摄从1994年到2002年历经8年,到2007年才制作完成。由于时间的沉淀,原本在冯艳看来不作为主线的秉爱的故事后来成了最重要的部分,而原先的主线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图3-8 《秉爱》
即便不是长期的拍摄,长期的关注也成为无限接近真实的重要条件。纪录片人黎小锋称:“纪录是时间的炼金术”[43]。在他的三部纪录片《夜行人》、《无定河》、《我最后的秘密》的拍摄中,他对于时间的积累于纪录片的意义有着深刻的体会。他的纪录片作品《我最后的秘密》从2000年开始试拍,集中拍摄是在2003年到2005年,2008年剪辑完成。从开拍到完成的8年时间里,真相才慢慢抽丝剥茧。在开拍的3年里,被摄者始终没有真正敞开胸怀。这个89岁的老太太总是喜欢讲她当年作为豪门之女、体育王后,有多少仰慕者追随,而她又如何违背父命,从上海逃婚到苏北,吃尽了苦头。但无怨无悔,与老先生过得怎样幸福。而在一旁的她的保姆却似乎有异议。而当黎小锋2003年开始频繁地访问的时候,真相才得以揭开。那个她抛弃所有而为之私奔的老先生,后来一直在背叛她,她几次自杀未遂,用六字总结自己的人生是:“错错错!恨恨恨!”而她所一直塑造的完美的主仆关系在她对保姆当面的训斥中粉碎。她曾立下遗嘱,将自己与老先生的全部财产为当地大学成立一个奖学基金,无儿无女的她惟恐她远房侄女与保姆知道后都不再理她,因而坚守着这个秘密,而事实上所有人都暗自知道了这个秘密。保姆趁老太太迷糊之际让她写下了2万元的馈赠字条,为了得到这笔钱,本不识字的保姆开始每天学习一个汉字。[44]这个由长时间的积累、深入的探究所揭开的真相,使两位老人相依又相斥的关系,人性中的复杂与多变充分展现出来。而如果没有长时间的观察,没有对真实锲而不舍的探寻,就没有后来的真相。如果这部纪录片停留在最开始的看上去的“真实”,那么将会形成怎样一个充满了谎言与假象的纪录片。黎小锋将这种时间的沉淀也运用到自己其他的纪录片中,比如纪录片《夜行人》——一部记录盲人母女生存境遇的纪录片的拍摄,前后花了四五年的时间。

图3-9 《夜行人》

图3-10 《我最后的秘密》
独立纪录片创作中时间的积累是大多数电视台纪录片尤其是栏目化的纪录片无法相比的。段锦川就曾批评某电视台拍摄的《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题材挺好,但是拍得非常糟糕,太仓促了,三天五天拍了一次,过了一个月又去拍了两天,就完了,弄了一个50分钟的”。事实上,这种短平快的制作在电视台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体制内的电视台中,留给纪录片长时间创作的空间实在有限。只有少量电视台仍旧划拨特别的经费支持一些专门创作纪录片的工作人员,只是体制内能够提供这种理想化创作环境的情形越来越少。严格规定了长度、制作周期的纪录片栏目化的结果使纪录片的“创作”成为了模式化、批量化生产下的“制作”,在稠密的播出周期的限定下,纪录片对现实的观察不可避免地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层面。当然纪录“时间”长短并不是绝对的,这取决于不同题材、不同对象的不同需要,也要视所要纪录的对象的价值来评判。
三、坚持——执著与超功利
独立纪录片的创作作为一种没有外在义务与责任的个人行为,需要极大的耐力。中国独立纪录片人为了探究与发掘真实而体现的一种执著、毅力和坚持,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纪录片的希望。
这里的坚持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面对复杂社会的各种表现,调适心理,坚定地拍下去。小川绅介说,当现实的一张脸突然间剥落的时候,你会看到很肮脏的一张脸。如果产生厌倦情绪就会想到放弃拍摄。但是,当坚持下来,把这张脏脸剥下来以后,就会看到闪光的东西,看到赤裸裸的人身上的光亮。在古屋敷村,当遭遇寒流,稻子被毁,小川以为村里的女人们会不得已出去卖身来过活,可事实却正相反。稻子遭了寒流的袭击,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救了整个村子,因为村民们可以拿了国家的救灾款过得比种地更舒服。当时小川觉得这些现象非常丑陋,甚至一度要放弃拍摄。但随着村民们一起过了这一关之后,小川才真切地了解了那些人的心灵是怎么样的。[45]
而面对被拍摄者的不配合,同样需要极大耐力坚持下去。早期创作者蒋樾在拍摄纪录片《彼岸》时,牟森培训班的解散,理想的破灭对于怀着明星梦的女孩段雪渊来说刺激很大,也因此蒋樾对她的采访屡屡受阻。对方总是跟蒋樾较着劲,不肯配合,而蒋樾坚持不停地跟她聊,就这样,拍摄了两盘几乎作废的磁带后,蒋樾的坚持慢慢地打开了这个孤僻的女孩心灵,她谈了自己的想法、命运与理想,而这些后来成为纪录片《彼岸》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另一方面,纪录片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寂寞的等待与发现的过程,是需要超越物质欲望的过程,尤其是对于独立制作人来说。小川绅介的亲身经历足以成为中国独立纪录人的教材,同时也是大多数独立创作人的真实写照。小川绅介自称“一边过着那种脏水沟里的老鼠似的生活,一边坚持拍电影。”[46]小川绅介辞去了岩波电影制作所的工作之后,没有任何收入,只有靠夫人的收入生活,生活窘迫之极,但他仍然四处自筹资金坚持着自己的拍摄。
吴文光早期是靠电视台同仁的帮助,利用电视台工作时省下来的磁带,借电视台的设备来拍摄,免费借用朋友的机房作剪辑,有一次为了不被人发现,甚至三天三夜只喝一瓶水。“我是从自己掏腰包开始,用各种省钱的方式,不会住好的,吃也不会吃什么,然后有一点钱就拍一点”,“像游击队一样”[47]。蒋樾拍摄《彼岸》的费用来自自筹的资金,花费了十几万元,大多是靠自己拍广告所得。另外借别人的钱,很长时间才还上,而最后一分钱都没有收回来。[48]蒋樾对《彼岸》的整个拍摄过程一直是赚得了钱就拍,钱没了再去赚钱,周而复始。蒋樾生活上非常俭朴,常常连固定的住宿地方都没有,搬个地方就要抱着所有的素材带子跑[49]。相比较其他独立纪录片人来说,身为京都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冯艳毕业后本可以找到有闲而有钱的工作,而她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纪录片。“我回日本打工,做翻译,打字。……我就有些收入可以继续下去拍,就是这样往复。……挣几个月钱然后回来拍。生活费用我们就压到最低,除了路费之外就完全住在老乡家里。”[50]同为日本留学生的舒曼本可以顺利地边读书边工作,按计划获得学位的她毅然放弃了工作挣钱和学习深造的大好机会,拿出所有的积蓄,独自一人往返于东京、大阪、南京、上海、北京、河北、河南等地,纪录了一系列有关中日间战争遗留问题、对日索赔和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纪录片。关于这种独立纪录片人普遍的创作与生活状态,蒋樾说,一般这种状态只能维持两年,但我们已经坚持近10年。创作者纪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幕幕戏剧。胡杰在拍摄纪录片《远山》时,不断有矿主来威胁警告,他一直坚持到有一次子弹就刚刚从他耳边呼啸而过,才离开了矿山。

图3-11 《远山》
中国当下的独立纪录片人所处的创作环境简陋之极,没有任何物质条件可言,他们的生活简单而贫乏。但他们为什么能在这样的境况里,孤立无援地持续工作?至少有一点,他们不愿只沉迷于自我的世界,他们触摸到了他人的需要而且主动进入到与他人的关联之中。这里的他人往往是这个社会中不掌握权力的大多数,无法表达和呈现自我的普通人。同时,在纪录片的传播上,独立纪录片人也表现了超功利的品质。他们在拍摄完成他们的作品后并没有竭力争取播出以及在国内外评奖。例如康健宁在以低成本拍摄了《生活》(1995)、《阴阳》(1997)、《公安分局》(1998)《当兵》(2001)、《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2002)等多部作者立场的纪录片后却都选择暂时不在国内电视台播出[51](《阴阳》曾以90分钟的版本在日本播出),也不参加任何评奖活动[52]。

图3-12 《当兵》
小川绅介认为,“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一种靠真实纪录的眼光和勇气建立起来的力量,来带动社会中更多的人来思考和改变现状,所以它不应该只是个别电影人的事,应该集合起来,共同推动,形成力量。”[53]小川绅介的这个呼声在便携摄录设备DV出现之后,在中国的独立纪录中有了实现的可能。来自各个行业、多种背景的创作者凭着探寻真实的热情不约而同地加入到这个队伍之中,以不断壮大的力量丰富着纪录精神的内涵。
【注释】
[1]徐圻:《论当今中国三种文化形态及其关系》,《新华文摘》1999年第1期。
[2]参考孟繁华著:《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3]《周国平访谈录》,载《东方》1997年第2期。
[4]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页。
[5]同上,第10、30页。
[6]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9页。
[7]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1页。(https://www.xing528.com)
[8]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页。
[9]刘红梅:《什么样的人文关怀——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伦理观》,《读书》2006年第10期。
[10]《老头》影片简介,见《老头》DVD封面。
[11]朱日坤、万小刚:《独立纪录:对话中国新锐导演》,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12]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13]朱日坤、万小刚:《独立纪录:对话中国新锐导演》,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4]同上,第78页。
[15]黎小锋:《追问“直接电影”:黄文海访谈》,现象网,www.fanhall.com.
[16]黎小锋:《追问“直接电影”:黄文海访谈》,现象网,www.fanhall.com.
[17]让·路普·巴塞克主编:《电影辞典》(法国拉鲁斯出版社1986年首版)中的纪录电影条目。
[18]譬如,法庭对庭审双方口供的笔录,会议文书对会议内容的笔录,影视机械对现实直接摄影或录像的单个素材性镜头——犯罪现场的摄影或录像、科研对象的摄影或录像、传授操作技术的摄影或录像、文化遗产存档的摄影或录像,未加任何处理的同期声录音等。
[19]贾秀清:《纪录与诠释:电视艺术美学本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20]钟大年《:纪录电影创作导论》,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380页。
[21]弗里德里克·怀斯曼著,吴文光译:《怀斯曼的电影世界——美国纪录片大师怀斯曼谈纪录片创作》载于林少雄主编《多元文化视阈中的纪实影片》,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437、431—432页。
[22]同上,第436页。
[23]比尔·尼可尔斯著,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纪录片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24]高鑫:《电视艺术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25]格里尔逊为1926年1月出版的纽约《太阳报》撰写的一篇影评里,将纪录电影作了这番定义,在其后相当长时间里被当作纪录片的权威定义,同时也被收录于法国《电影辞典》中的“documentaire”条目。
[26]Bill Nichols,Movies and Methods:an Anth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 281.
[27]同上,p.234.
[28]同上,p.261.
[29]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1页。
[30]参考樊启鹏《:个人书写与民间影像——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与传播》,2007年博士论文,北京师范大学。
[31]刘洁:《〈的哥〉:折射生命的万象之镜——纪录片编导范俭访谈》,《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第5期。
[32]刘洁:《〈的哥〉:折射生命的万象之镜——纪录片编导范俭访谈》,《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第5期。
[33]刘红梅:《什么样的人文关怀——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伦理观》,《读书》2006年第10期。
[34]吕新雨《:什么是纪录精神》,林少雄编《:多元文化视域中的纪实影片》,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35]贾樟柯:《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南方周末》1998年。
[36]参考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3—235页。
[37]参考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3—235页。
[38]刘洁:《弥散着荒诞的世像——纪录片编导黄文海访谈录》,《南方电视学刊》(双月刊)2006年第1期。
[39]阿尔伯特·梅索斯(Albert Maysles 1926—)是一位著名的纪录电影大师,他和弟弟大卫·梅索斯(David Maysles 1932—1987)是直接电影的先驱者,他们一起拍摄了《推销员》、《灰色花园》、《给我庇护》、《奔跑的栅栏》等经典电影。
[40]张同道、李劲颖:《直接电影是纪录片最好的方式》,《电影艺术》2008年第5期。
[41]吴文光:《一种纪录精神的纪念——记日本纪录片制作人小川绅介》,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357页。
[42]《三个纪录片人的幸福生活》,阳光网媒,Http://www.chinasuntv.com。
[43]黎小锋:《镜子边缘的苍蝇:三部纪录片的创作札记》,《电影艺术》2008年第6期。
[44]黎小锋:《镜子边缘的苍蝇:三部纪录片的创作札记》,《电影艺术》2008年第6期。
[45]参考小川绅介著,冯艳译:《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6]小川绅介著,冯艳译:《寻求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多元文化视阈中的纪实影片》,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48页。
[47]方方著:《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
[48]参考吕新雨:《纪录中国——中国当代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9页。
[49]方方著:《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
[50]《三个纪录片人的幸福生活》,阳光网媒,Http://www.chinasuntv.com.来源:《南方周末》。
[51]2004年,《阴阳》和《当兵》的剪辑版(约60分钟)在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栏目播出。
[52]参考刘红梅:《什么样的人文关怀——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伦理观》,《读书》2006年第10期。
[53]小川绅介著,冯艳译《:收割电影——追求纪录片中主高无上的幸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