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女导演的历史洞察力
随着1976年“文革”结束,长期遭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精神逐渐复苏。复苏和觉醒的潮流首先在一批“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走来的老作家的创作中有着自觉地体现。
巴金历时八年著成《随想录》,从自身经历出发来反省“文革”,并由此展示出整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在50年代以后的精神历程。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当文艺界尚未普遍地自觉摆脱“文革”话语时,在文学界出现了“三只报春的燕子”。白桦的剧本《曙光》以历史悲剧借古讽今,率先揭开了几十年来压在人们心底的对极左路线的仇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以中学生的愚昧无知、简单盲从为警钟,写出了“文革”十年盛行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风尚对社会现实和国人精神所造成的深重危害;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则直接为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鸣不平,正面表达了对文化知识的尊重和对知识分子的赞美。一种新的文学和艺术的精神走向逐渐蔓延开来,中国政治和思想界的剧烈变化也体现着相似的趋向。
在这场理性湮没愚昧的浪潮中,女性知识分子也被赋予一种思考的使命和言说的机遇。70年代末的文学创作的主题精神呈献了对于以往作品很少论及的复苏的“人性”的思索、颂扬和赞美。这一艺术共性体现了人们在“文革”后的一种觉醒,一种要求对“人性”和“真理”进行重新思考的觉醒。
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觉醒,70年代末的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到关乎真理的讨论中去,以不同的方式完成着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和民族命运的个体承担和反思。在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力透纸背的笔墨,话剧领域也随着文学艺术史的这场“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了戏剧观念的探索和演剧方法的创新热潮。
戏剧女导演在其舞台艺术创造中同样呈现了主体对于时代政治和民族命运的思考。在对世俗和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中,在对各式各样的时代声音的辨析和反思中,在对自身信仰和理想的拷问和坚守中,戏剧成了一种有效的表达话语,一种时代的内心独白,一种关乎真理和变革的宣言。这一时期的舞台艺术和审美态度,无所谓教化、宣传,无所谓主旋律,无所谓正统、保守或者前卫,依靠它,导演用以完成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是对于时代政治和历史选择的个体态度。

图82 导演苏乐慈
这场源于真理的讨论,曾因1978年5月《光明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有过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辩论。辩论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中国文联及五个协会正式工作的恢复。这一时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伤痕文学”的提法随即开始流传。与“伤痕文学”同样深深印刻在历史的记忆中的还有一场影响全国的话剧演出。这就是苏乐慈导演(图82)和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业余作家和演员共同创作演出的话剧《于无声处》。
以“天安门事件”[1]作为时代背景所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的上演,如同惊雷,震撼全国。《于无声处》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的上演和紧接着受到的全国性的狂热关注和认同,吐纳了一种压抑已久的全社会的时代共鸣,标志着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群众代言人的身份重新确立起来。从年长的到年老的几代艺术家以复活了的政治激情和政治勇气来直面现实人生和民族命运,重新凝聚起戏剧的现实批判力量,感召了一场正在酝酿和进行之中的正义的全国性的政治变革。
剧中有关“文革”十年的反省,对“四人帮”的仇恨,正好契合了时代的共同脉动,因而,当《于无声处》在舞台上勇敢地发出“时代之声”的时候,它所引发的空前的时代共鸣和反响,令这个话剧超出了艺术的范畴,继而成为当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构成部分。1978年,首演成功后的《于无声处》晋京演出(图83),盛况空前,首都上千名群众从工厂、郊区、机关、学校,拥向剧场。演出开始前,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写下诗文、在英雄纪念碑前奉献花圈的人们,相会一处,热情感慨,互致问候,重温1976年那段刻骨铭心的时刻。

图83 北京文艺界及人民群众在北京火车站热烈欢迎《于无声处》剧组晋京演出的历史场景
话剧《于无声处》诞生于上海工人文化宫的戏剧教学的课堂里。当时的苏乐慈导演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表导学习班的教员。那个时期的群众文化非常活跃,每逢周末都有从上海的四面八方赶去工人文化宫进行戏剧训练的普通工人,这些工人里面就有《于无声处》的作者宗福先。可以说,《于无声处》是当时上海群众文艺教育的一个意外的成果。编剧班的学生在完成学业的时候需要递交毕业作品,在众多的毕业作品中,苏乐慈导演一锤定音地选择了《于无声处》。剧本严谨的“三一律”的结构方法,缜密的情节构思和跌宕起伏的时代沉浮中的人物命运一下子吸引了导演的目光(图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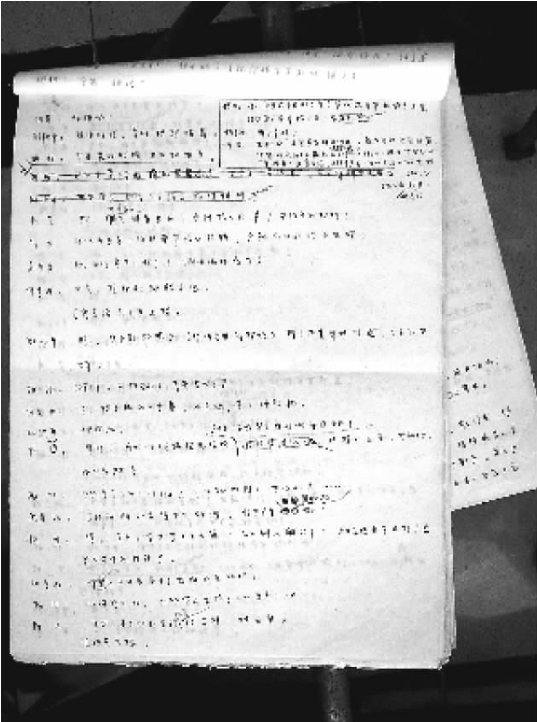
图84 《于无声处》的剧本手稿

图85 鲁迅先生书赠日本友人的《无题》诗
《于无声处》以四幕的结构展开叙事,运用严谨的传统“三一律”的结构方法,以1976年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为背景,通过两个家庭、六个人物、九个小时之内,在一间客厅所展开的纠葛与冲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场斗争的本质,揭示了“人民永远不会沉默”这一历史真理。该剧的剧名出自1934年鲁迅先生书赠日本友人的《无题》诗。诗云:“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图85)蕴含在剧本中的巨大的精神解放的激情和力量,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和斗志,感动着导演,点燃了导演的创作激情。在这种激情和勇气的推动下,一个毕业作业经苏乐慈导演的排演,很快成了当时教学的成果,而这个优秀的教学成果不期然地演变成了时代转型的助推。
故事发生在1976年初夏。老干部梅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身患癌症。梅林之子欧阳平陪她赴京看病,途经上海看望老战友何是非一家(图86)。而此刻,何是非的女儿、欧阳平曾经的恋人、公安人员何芸,正奉命侦缉一个在“天安门事件”中散发传单的“现行反革命”,而这个“现行反革命”事实上就是梅林之子欧阳平。欧阳平出于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慨,参加了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编印并且散发了诗集《扬眉剑出鞘》。欧阳平和母亲(图87)此时并不知道,正是这位“战友”,于九年前诬陷梅林为叛徒,现在又已投靠“四人帮”。何是非不仅诱逼女儿何芸断绝与欧阳平的旧情,和一个“四人帮”的亲信订婚,并胁迫何芸亲手逮捕欧阳平。欧阳平临危不惧,坚持斗争,促使何芸认清了“四人帮”的阴谋,鼓舞了一度消沉的何是非之子何为振作起来。何是非的妻子也终于觉醒,揭发了丈夫曾诬陷梅林的卑劣行径。何是非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图86 《于无声处》剧照

图87 欧阳平与母亲梅林
1976年9月23日,饱含着时代之子爱与恨的《于无声处》在上海一座老式建筑——上海工人文化宫首次上演(图88)。前来观摩的大多是工人,也有老干部、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开始,场内交头接耳,有些嘈杂,秩序并不是很好。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和发展,观众渐渐安静下来。当老干部梅大姐带着因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而被通缉的儿子,投奔自己的老部下何是非,即将遭到公安人员抓捕(何是非告密)时,观众开始着急了,他们迫切希望梅林的儿子欧阳平赶快逃走脱离险境……当公安人员赶到,欧阳无法脱身。生死离别之际,母亲拥抱儿子,鼓励他“勇敢地去到法庭上,和他们作一场最后的斗争”!此时,剧场里响起悲壮的《国际歌》,观众席上,许多人开始哭泣……结尾,何是非的妻子、儿子、幡然醒悟的女儿何芸,毅然决定和欧阳平站在一起时,何是非颓然瘫于椅子上。天空中,隆隆的闷雷声此起彼伏,越来越近,最后变成惊天的炸雷,于无声处听惊雷,惊雷撕裂黑暗的力量象征了“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https://www.xing528.com)
图88 当年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门口排队观看《于无声处》的景象
以“伤痕文学”为发端的“文革”后文学,在开始阶段里从时间上极其巧合地配合了政治上“改革派”对“凡是派”的斗争。“伤痕文学”以鲜明的立场表达了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及对相关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这种真挚而深沉的现实情感在广大群众中获得强烈反响,成为“改革派”否定“凡是派”的有效的文化武器,在短短一两年中,文学和艺术创作得到极大繁荣,在批判现实方面达到了50年代以来所没有的深度和强度,由此展现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罕见的高扬。
《于无声处》也以其在特殊时代,知识分子失语状态下依然坚持个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立场的品格,呈现出了“文革”当中年轻一代的独立思考和求真意识(图89)。和“文革”时期那些“潜流”写作的文学源流一样,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制约而回到个体的现实生活体验、想象和严肃的思索之中,由此显现出人性和意识的觉醒。以复活的政治激情和现实勇气直面现实人生,重新凝聚起现代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力量,对“文革”所带来的弊病给予大胆地暴露和批判,把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审视现实的批判眼光结合起来,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全社会同仇敌忾的历史对立面。苏乐慈导演的《于无声处》,因其在历史重大转折期所显示出来的历史洞察力和现实影响力,注定要在史册上留下浓浓的一笔。

图89 各种版本的《于无声处》

图90 30年前的合影。左起:苏乐慈、宗福先、张孝中、周玉明

图91 复排《于无声处》的演员阵容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认为这出紧密结合时代政治的话剧,这出严格地按照“三一律”所结构的写实话剧,会伴随着政治生活的转变而逐渐为人所淡忘。出人意料的是,为纪念《于无声处》30年前的演出(图90),2006年上海话剧中心复排了这出话剧(图91)。30年过去了,主人公欧阳平在那个特殊时代中的遭遇和选择依然牵动着观众的心。关于人性中那些永恒的道德和高尚,以及卑微与渺小,依然在30年后的人心中经受着审判。这出戏之所以显现了穿透历史的生命力,也许正如导演所讲的那样,它并非仅仅是一部反映时代政治的话剧,它最深刻的意蕴也许是通过一种特殊政治背景下的人的选择,提炼了一种存在于民众心中普遍的关于真善美,关于道德操守,关于道义人情的理想和追求。

图92 《屋外有热流》剧照

图93 《屋外有热流》剧照
《于无声处》之后,社会开始关注这个话剧创作群体,都等待着这位年轻女导演的下一个戏。但出人意料的是,1979年苏乐慈导演拿出来的却是个“另类戏剧”——贾鸿源、马中骏、瞿新华合作创作的《屋外有热流》(图92、图93)。这部话剧从剧本主题、演出样式、美学风格与《于无声处》截然不同。《于无声处》是触及时代精神的最尖锐的政治题材,《屋外有热流》却是完全无关政治的道德伦理剧;《于无声处》采用的形式是最传统的“三一律”,《屋外有热流》却是全国最早突破时空限制,把过去、现在与将来,把现实与想象,把活人与鬼魂全都放到一个舞台框架里来表现的探索戏剧。这出颇具荒诞色彩的话剧演出,表现了一个插队落户的知青不幸去世后,其灵魂回到故乡上海后的所见所闻。他看到了家中即便是坐在火炉上还瑟瑟发抖的“怕冷”的兄弟姐妹,鬼魂以自己的方式鼓励这些蜷缩在屋里的怕冷的青年走出屋子,走向充满热流的社会和人生。剧本真实地反映了“文革”后内心有着创伤,心有余悸的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在内容上具有深刻的内在隐喻,在形式上有着重大的创新。但是,体现在剧本中的导演思想,依然积极地指向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地朝光明的方向转变的信念。《屋外有热流》成为了新时期话剧演剧艺术观念创新与形式革新的历史选择中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索戏剧的重要代表作,其观念和形式的革新甚至早于北京人艺的《绝对信号》。为了肯定这出戏的特殊的意义和贡献,肯定其在戏剧美学观念上的创新和突破,文化部在当年,为其增设了一个特别的奖项。
紧接着,苏乐慈又导演了《血,总是热的》,时年恰逢“改革文学”盛行,《血》剧从题材到内容又切换到了呼唤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主题上去,戏剧手法上采用了“无场次话剧”,探索和形式承载了政治主题的戏剧内容,《血,总是热的》成为苏乐慈导演的又一部代表作品(图94)。如果说话剧《于无声处》表现了时代的共同的呼声,像一声惊雷,震动了千万人民的心弦,那么苏乐慈导演的话剧《血,总是热的》,切中了时代的“危机感”,像震耳的警钟,唤醒坐等“四化”的人们,齐心协力、同心同德进行没有退路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背水一战”,“只有这样,中国的改革才有希望。”整个戏流动着一股深沉而炽烈的振兴民族的感情。反映在企业管理上革新与守旧斗争的大型话剧《血,总是热的》,还紧紧扣住了时代的脉搏,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一些本质的东西,给人以启迪。剧终,观众缓缓挪步,剧中罗心刚的话语似乎依然在耳边回响:“中国怎么办?没有退路了,只有靠我们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和中国的志士仁人一起,……拼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来!”

图94 《血,总是热的》剧照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悲惨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使知识分子重新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同时又激发起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时期,“改革”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和社会共名。就社会思潮而言,“改革文学”是中国人在打破精神迷梦之后的历史文化的新产物,这个刚从迷狂中清醒过来的民族,需要通过经济复苏和精神振奋来编制新的希望和蓝图,重建精神家园和信仰系统,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心。《血,总是热的》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真谛的探求,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探讨,沿袭了导演一贯紧扣时代命题,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选择。
苏乐慈导演和剧本的原创者们深入工厂,采访厂长、劳模和普通工人,寻找生活原型和形象种子。他们发现,当时,凡是那些想多干事情的厂长都有着共同的苦衷,都有一些难言的叫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他们都面临着“解决眼前一个问题,但同时却会冒出五个新问题”,碰到许多“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事情。看到生活中有那么一批像罗厂长这样有思想、有才华的共产党人,在用自己的热血当润滑剂,让“中国这架咬死了、锈住了的庞大机器”更快地转动起来。导演被深深感动了,她把自己对改革者的敬佩之情注入舞台,真诚地讴歌了在改革举步维艰的时刻,共产党员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尚情操和牺牲精神。对生活的探求和对艺术的探求,使导演能传神地集中人物的思想,发出饱含哲理的议论,生出绝妙的点睛之笔。
剧中那以不同身份出现的“制度化身”“官僚主义化身”式的人物,人物形象的一言一行,使观众在苦笑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凡是看过剧本的人,大都认为《血》这个剧本颇有深度,思想容量很大,但同时会感到二度创作的难度,光场景就有17场,舞台上有名有姓者达17人之多。怎样既能完成严谨流畅的叙事,又能创造演出艺术的完整性是摆在导演面前的大难题。苏乐慈导演根据剧情需要,在舞台装置上采用多层次多块面平台,打破了过去话剧分幕分场的传统形式,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充分调动观众的思维能力,作了新的尝试(图95)。导演认为,生活的节奏加快了,人的思维加快了,观众已不习惯“听我慢慢道来”的传统舞台叙事方式,话剧舞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叙说方式必须探索和拓展。

图95 《血,总是热的》剧照
在她的指挥下,排练场充满着浓厚的创作气氛,来自各工厂、基层单位的业余演员们,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感受到了剧本所蕴含的有识之士心中的呐喊,演员们的创作热情异常高涨。隆冬之夜,演员们一下班就匆匆赶到工人文化宫,通宵达旦地排练。扮演罗心刚的演员,是当年在《于无声处》中扮演欧阳平的张孝中,他醉心于塑造罗厂长的角色,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在边演出、边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导演对演出文本三易其稿;舞台上,大、小改动几乎每天都有,编导演舞美通力合作,排练创作的过程洋溢着具有80年代特征的对于艺术的忠诚、执著和激情。
苏乐慈导演和她的话剧创造团队,同那个时代的所有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一样,在步出“伤痕文学”的阶段之后,转而跃入了“改革思潮”的新的时代洪流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苏乐慈导演的两个创作阶段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艺术特征,那就是依仗着强大的时代精神和共名而生,作品往往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或民众的普遍精神情绪的代言人,同时又担当着历史正义和良知的捍卫者的重要角色。
与50年代的艺术家们不同的是,50年代的舞台艺术家们的作品中充满了革命主义和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融的总体气息,然而,有时他们的声音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话语的同声传播。而“文革”后的创作虽然仍旧体现出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生活的强烈参与精神,坚定不移地宣传改革政策的必要和必然,但是,对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理性批判变得更为自觉。这种自觉地批判和反思,涉及了对执政党内的权力斗争和社会腐败风气的批判。作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表现改革与人心世态、风俗习惯的变化,从理想主义的阶段过渡到更加现实和深沉的阶段。

图96 导演雷国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