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关键节点,中国现代档案学科、现代档案学高等教育以及诸多现代档案管理实践活动均在此阶段产生,被视为中国档案事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传统史家的理想、乾嘉考据学派所蕴含的科学求真精神、五四前后西方实证方法与科学史观的传入与模仿、内阁大库档案的遭遇与整理实践、“公共心”的提倡和图书馆博物馆事业的拉动、外国档案馆事业的专业见识、行政效率提高的呼声等多种因素,共同营造了近代档案思想形成的人文环境,促进了我国档案事业的专门化和档案学的萌芽。[86]巧合的是,受欧美新史学、图书馆学、行政学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部分开明人士先后提出了创建中央档案局、国立档案总库的设想,甚至草拟了《档案保存法》《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等法律文件,掀起了一场持久倡导国家档案馆建设的思潮,虽最终未能建立国家档案馆,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美国等新兴国家掀起的公共档案馆或国家档案馆运动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可以称之为“国家档案馆运动”。
早在北京政府初期,外交部等中央机关就开始设置“档案库”来保管本机构的重要文书档案[87]。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国图书馆界在推动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同时,试图将国家档案文献的保存纳入中央图书馆的管辖范围,从而形成了我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档案馆的初步认知。1928年12月,时任外交部长兼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的王正廷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设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其草拟的《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组织大纲》的规定,中央图书馆负责“搜罗党国史料,整理档案”,“设立共同保藏档案图书场所,保管档案及图书,并办理借索档案及图书事宜”[88]。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金陵大学召开,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员的蒋一前提出了《呈请政府组织中央档案局案》,这份议案比较简单,主要阐述了政府组织中央档案局的理由及方法。对于为何要创建中央档案局,他认为,“整理档案以供现时之参考,为当今之要务。而各部各地,整理异法,既不集中易致遗失,且亦不便查阅”,因此“非设中央档案局,不足以救其弊”。“档案为一国之文献,宜设专部典藏之”。他认为传统的档案管理办法“专恃一、二人之脑力”,“不但整理不得完善,甚至移交亦不可能”。因此,“宜设中央档案局,参考科学方法,采用标准检字及规定索引整理之,以为全国之模范”。而如何组织中央档案局,他建议中央档案局隶属于中央图书馆,并从组织框架设计、经费与建筑等方面提出了参考意见[89]。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关于成立国家档案行政管理局的提案。《申报》对此也进行了简略的报道[90]。从议案的基本内容看,至少传递了如下信息:第一,不少档案保管与整理机构存在档案的自然损毁、人为破坏甚至被盗等状况,档案管理状况不容乐观;第二,缺乏有效的制度来保障机关文件向档案室(馆)的定期移交。这些状况表明,当时国民政府各机关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缺乏规范与制度的状况之下,缺乏有效的档案行政管理体系。因此,蒋提出筹设中央档案局,应当来说是切中要害,是一剂治理当时中国政府机关档案管理问题的良方。蒋一前毕业于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是一位汉字检字法专家,在他所撰写的论著中鲜有关于档案学方面的内容,因此目前很难找到有关他撰写这份议案的背景信息。不过,根据1929年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的记载,蒋一前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促成中央图书馆早日实现案》,理由之一是“档案不集中,不便于各部参考”[91]。时任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袁同礼提出了《请各省市政府调查及登记所属区域内所藏之书报绝板及档案遇必要时设法移送图书馆保存案》,要求将“无人注意”“损坏甚巨”的档案,在必要的时候“得移送图书馆保存”[92]。据此可以推测,当时中华图书馆协会正在筹建中央图书馆,并且协会的领导层比较认同中央图书馆应当承担保存历史档案的责任[93]。
国民政府内部存在提倡行政效率运动的改革派以及专注于创建国史馆的开明派人士,他们就国家档案馆建设也提出了有建设性的议案与想法。由于明清历史档案、北洋政府旧政权档案的保管混乱等问题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930年国立北平研究院上书教育部要求对历史档案妥善保存,不能任意销毁或贩卖,并指出:“欧西各国对旧有档册,即一鳞一爪,莫不设法搜集,建设专馆,加以保存。”[94]这里的专馆应指西方国家的国家档案馆或国家历史档案馆。1934年1月,邵元冲、居正、方觉慧等人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重设国史馆案》的议案,该议案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转交国民政府行政院审核,3月底行政院内政、教育、财政三部会审后认为,“旧式国史馆之意义已甚微薄”,而“官撰新式国史,尚非其时”,限于人力、财力等困难,“今日在国史整理上之需要者,不在国史馆”,因此建议重点做好两件事情:“一、搜索史料及整理在时间上已可公开之档案,应委托学术机构从事,作为一种科学工作”,“二、未到公开时期,而不专属任何机关,或现属某机关而堆积不用之档案,应设立直隶于行政院之国立档案库……以保存国家文献”。[95]这是国立档案库第一次被南京国民政府在公文中正式提出来,尽管“国立档案库”的提案未能变为现实,不过有关国立档案库功能与想法的讨论依旧在进行。滕固认为国立档案库的价值不可估量:“有了国家总档案库搜罗时间上较古而现行机关不恒取用的档案。此在消极方面,可补救独立机关因堆积而损失的情事;在积极方面,替历史学者设置了一所贵重的作场。”他甚至希望仿效德、奥、瑞士诸国,将这一体制推行到地方“而有地方档案库之设置”。[96]1935年10月,历史学家蒋廷黻发表《欧洲几个档案库》一文,专门提及了德国柏林的两个大型中央档案库:普鲁士档案馆和帝国档案馆[97]。1939年1月,张继、吴敬恒、邹鲁等十三人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档案总库筹设国史馆提议》的提案,重提国立档案库的建设问题。该提案认为,“夫欲续历史,不可不设国史馆;欲保存史料,不可不设档案总库。盖国家档案为史料之渊海,国史之根抵(柢),实为至高无上之国宝”,并参考西方当代国家档案馆和中国古代架阁库等制度,主张将“总档案库设于国民政府,所藏皆各院、部、会之机密重要档案正本,府文官长管其钥,更师古代金匮石室遗意,特造钢骨水泥之地下库,而以铁匮藏其中,国之重宝可同藏焉。各院、部、会各自藏其副本,俟时效已过,或取出发表于时政记,或终藏于总档案库将来择其宜者作为史料”,而针对可公开和不能公开的两类不同的档案,提案主张“宜采英国蓝皮书制度,将全国重要案卷分为二类:一为当时可发表者,即印于蓝皮书(案:蓝皮书之名可取唐宋时政记之名,易之说,详下)而公布发卖,使国民咸知……一为秘密档案,一时不可发表者,则存于特别档案库而严密保存,将来即可用为史料”[98]。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中央档案局、国立档案库、国立档案总库的设想均未能变为现实,但以张继等为首的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及后来的国史馆一直在为国立档案总库的筹建进行着扎实而积极的准备。《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筹备大纲》将“筹备档案总库”“整理档案办法”“筹备时政记”作为筹备国史馆的重要任务[99]。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先后推动国民政府颁发了《国民政府关于废存旧档移交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保存的训令》(1941年5月)、《各机关保存档案暂行办法》(1941年10月)、《国民政府通饬各机关清理档案的训令》(1945年9月)、《国民政府关于接收党政军机关旧档》(1946年2月)等文件,从制度上保障了历史档案与机关现行文件向国史馆的正常、有序移交,使国史馆实际上承担起了中央档案馆的责任。
此外,傅振伦和毛坤开展了我国最早的国家档案馆制度体系的设计工作。傅振伦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20世纪30年代两次赴欧洲考察,参观过英国公共档案馆和法国国家档案馆等欧洲著名档案馆,1940—1942年受聘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任编纂干事,翻译了“欧美档案馆学论文译丛”10篇:《德、奥、瑞档案馆考察报告书》《美国中央档案馆概况》《美国中央档案馆法案》《美国移交中央档案馆之档案整理条例》《美国中央档案馆中档案之修整及保藏》《欧洲档案馆之编目》《普鲁士档案学教育之养成》《柏林普鲁士史学专科及档案学学院规程》《普鲁士国家档案馆档案学术服务人员录用法》《关于苏联之档案机关》。傅振伦对各国档案管理体制进行了简要介绍。例如,德、奥、瑞士诸国的“总档案馆与地方档案馆,均直隶于全国档案总董,而不隶属于科学教育艺术部总长”,苏联“中央及高级机关之档案,政治上、学术上具有重大价值之地方档案及地方档案机关管理不利,易致损害之档案,均得由中央档案机关接管。盖采中央集中保管制度也”。[100]傅振伦草拟了《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该条例分五章二十一条,其中在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国家档案由“国家档案馆、省市档案馆、县市档案馆”保存管理,从而明确提出了国家档案馆网的构想;第二章第三条规定,“国家档案馆直属于国民政府,并受全国档案监理会之指导监督”,这一制度设计显然受到德、奥、瑞士诸国国家档案馆直隶于“全国档案总董”做法的影响;第二章第四、五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具有全国性质者”、“具有重大价值者”的档案,国家档案馆下设总务处、编辑处、典藏处、修整处、流传处,以做好国家档案馆的日常业务与行政管理工作[101]。
毛坤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又在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攻读图书馆学,1934年任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档案管理特种教席的中方教师,主讲《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学》等课程,是国内最早主讲档案管理学课程的中国人。毛坤深受英国古典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的影响,崇信“档案必须在某种完善可信之档案管理系统中传下者方为可靠。经过私人及不完善之档案保管室收藏者,即有流弊”[102],因此非常关注国家档案馆建设。由于授课的需要,毛坤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档案管理的书刊,并深入档案管理部门实地考察,逐步形成了对中国档案管理体制的构想。1936年,他发表了《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一文,明确指出:(https://www.xing528.com)
管理档案处的行政组织系统,我以为要分为独立的档案管理处和附属于某机关的档案管理处。独立的可暂分为全国档案管理处、全省档案管理处和全县档案管理处三级。全国档案管理处直隶于国民政府或行政院,全国各机关的老档,概行送归管理。全省档案管理处直隶于省政府,全省各机关的老档,概行送归管理。每到一相当时期,全省档案处应将所储档案目录送呈全国档案管理处备查。……全县档案管理处直隶于县政府,全县各机关的老档送归管理。[103]
由此不难看出,毛坤所谓的全国档案管理处、全省档案管理处和全县档案管理处,相当于各级国家档案馆与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集合,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认为,“档案之为物,时间愈近行政上之功用愈大,时间愈久历史功用愈大。所以现档当然留在机关中作行政上的参考,老档相对于该制档机关效用甚微,但对于历史社会学者之研究价值却甚大。正是己所不用而人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送到一个总机关去保存应用”。1939—1940年,毛坤就借鉴欧美国家档案馆的管理办法,参考当时故宫博物馆文献馆等机构管理清代档案的经验,结合个人创见,草拟了我国最早的一份《国家档案馆规程》,该规程包括创建规程、组织规程、工作规程、人事规程、征录规程、编目分类索引规程、藏护规程、应用规程、编印规程、销毁规程十章,并列入了其1940年撰写的《档案行政学》讲义当中(参见图1—1)。他在《档案行政学》讲义中指出:“为免除空言而较合实际起见,对于档案行政一课,特草拟《国家档案馆规程》一种,将可能想到之档案行政中之各项问题尽量纳入,使行政理论有所附丽。”[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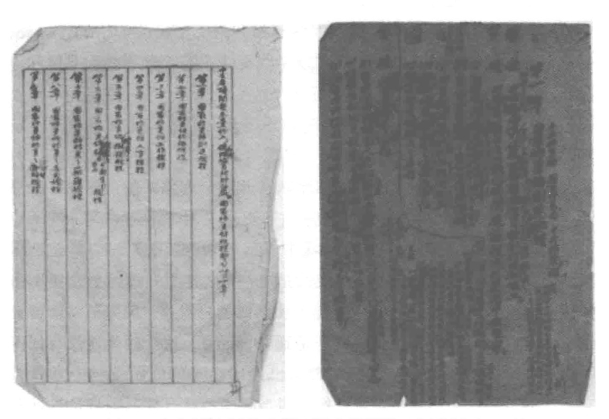
图1—1 《档案行政学》讲义中的《国家的档案馆规程》(四川大学校史馆收藏)
从这份《国家档案馆规程》的框架来看,前四章是针对国家档案馆的整体管理而言的,后六章则是面向具体的档案管理流程。毛坤在教学实习中,安排学生模仿《国家档案馆规程》来草拟省立档案馆规程、县立档案馆规程及机关档案室规程,为民国时期档案管理工作走向科学化、专业化提供了基础[105]。在此期间,起草《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的傅振伦于1942年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辞职,并于1942—1944年短暂任教于迁至重庆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档案馆制度建设的两个代表性人物汇聚于重庆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体现了该校档案学教育的重要地位,而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傅振伦写出了《公文档案管理法》这一中国近代档案学名著,对国家档案馆的选址原则、建筑形式、库房设备和管理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106]。当代著名档案学者邓绍兴等对此评价甚高,他认为以毛坤为代表的“文华档案专科班突破了当时档案学局限于研究现行机关档案集中管理的小圈子,提出了国家档案馆网的设计意见,主张设立独立的档案管理处和附属于机关的档案管理处,相当于国家档案馆和机关档案室,以使档案的宏观管理趋向专业化和科学化”[10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